2025-05-25《论神性》:我看到了真理的影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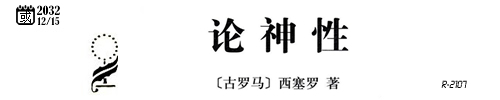
我要求每个人都到庭,来掂量掂量这些证据,然后作出判决:我们应该怎样谈论宗教、虔诚、神圣、祭仪、信仰和誓言,怎样谈论我们的神庙、神龛、庄严的祭祀,甚至谈论我自己主持过的占卜。
——第一卷
对于宗教、虔诚、神圣、祭祀、信仰和誓言,我们如何谈论?对于神庙、神龛、庄严的祭祀甚至占卜,我们又该如何看待?如何谈论和如何看待成为问题,而这个问题指向的是一个关于神的本质问题:“所有这些事都与不朽诸神的存在和本性问题相关。”也就是说,这是和诸神的存在、神的本性相关的问题,对于如何回答这些问题,如何解决疑问,西塞罗希望每个人都能从这些证据中作出判断,而判断就需要“每个人都到庭”,“到庭”就意味着掂量大家提供的证据,然后对不同的观点进行判断,而西塞罗在公元前77年的时候就有了“到庭”的机会,那就是在朋友科塔家中参加了一场关于神性问题的讨论会。
那是在“拉丁节”期间,参加讨论会的人有主人科塔,还有议员威莱乌斯,还有巴尔布斯,“让科塔去判断我们从斐罗那儿学到的东西吧。”科塔、威莱乌斯和巴尔布斯都是历史中存在的真实人物,西塞罗比他们都小,不同时代的人“到庭”,实际上不管是讨论的时间还是讨论会本身,其实都是西塞罗的一次虚构,之所以虚构就在于实现“每个人都到庭”的目的,而将不同的观点记录下来写成此书,更是为了让更多的读者“到庭”,从而从他们提出的观点和证据中作出判断。所以虚构本身就强烈表达着西塞罗的意图:威莱乌斯是伊壁鸠鲁学派“在罗马的最伟大的代表”,巴尔布斯则是“斯多亚学派哲学的专家”,是“讲希腊语的斯多亚学派的代表人物和领袖”,也就意味着西塞罗所要记录的证据就是威莱乌斯代表的伊壁鸠鲁学派和巴尔布斯代表的斯多亚学派关于神性的观点。
当然,西塞罗参加这次讨论会,他也带着关于神性的问题,“关于诸神显现的形象、诸神的家园和居所、诸神的生活方式,都有许多不同的理论,这些理论也都是哲学家们不断争论的话题。”伊壁鸠鲁学派和斯多亚学派是希腊古典哲学的两大流派,在罗马时期也具有极大地影响力,对于神性问题,两派也有各自不同的观点,在西塞罗看来,他们争论的关键与核心是:“诸神是否什么都不做,什么都不关心,超然于世界之外,也不照料和管理这个世界;或者持相反的观点,万物皆由诸神从时间之初创造构成,并将永远由诸神来管理和统治。”这个争论的焦点在首先阐述的威莱乌斯那里,就变成了他对巴尔布斯的疑问:斯多亚学派认为有一种“神意”,如果柏拉图所说的神相同,那么它的动力和工具是什么?如果不同,为什么它要创造一个有时间的世界,而不是如柏拉图的神那样“创造一个永恒的世界”?
疑问本身就是一种对斯多亚观点的否定,甚至威莱乌斯认为这些观点是“愚蠢”的:如果宇宙本身就是一个不朽的存在物,而且是最美的球体,“而我却觉得圆柱体、正方体、锥体或者三棱锥更美。”如果世界就是一个神,而世界也有沙漠和冰雪,那么,神的一部分被烧烤着而另一部分被冷冻着?如果所有自然元素都服从神的意愿,神利用光线和天体装点宇宙,那么他以前是不是一直生活在黑暗之中?威莱乌斯的这些质问其实都指向了斯多亚学派的“神意”,他列举了从古希腊哲学第一人泰勒斯开始的自然哲学,如果诸神会发怒,如果诸神间存在战争,如果诸神有悲痛,如果诸神将欲望演变为人类的交媾从而使人类将诸神认做父母,那是不是反倒变成了一种迷信?“这些东西都源于对真理的无知。”
在威莱乌斯看来,“愚蠢的人”都应该尊敬伊壁鸠鲁,他才是神圣存在者之一,因为他认为,之所以诸神存在,是因为“自然自身已经将诸神的观念刻在了每个人的心灵中”,这种观念是普遍赞同的“内在观念”,是关于神的“先在的知识”,伊壁鸠鲁将这种观念称为“先觉”,先觉就是根植于心灵中的知识的确定形式,“没有这种内在的知识就不可能有其他知识,也没有理性的思想或论证。”所谓诸神的存在,实际上就是这种“先觉”的存在,所以威莱乌斯认为,诸神所具有的就是人形,这才是神的本性,即神性,“不管是醒着或睡着的时候,诸神还曾以其他形象向我们显现过吗?”诸神拥有人的形象,这种形象不是躯体但类似于躯体;它没有血液,但有某种类似于血液的东西;诸神的快乐是拥有美德的快乐,美德是理性的必然,所以理性只与人的形式有关。在这个意义上,威莱乌斯认为,伊壁鸠鲁就是藉着他的理性把握了这个被深深遮蔽着的真理,而真理被揭示、被把握的意义就是:“我们必须用理智而不是用感觉去把握诸神的活生生的本质。”
| 编号:B32·2250414·2284 |
这就是伊壁鸠鲁对人类恐惧的拯救,赋予了人类的自由,“我们知道它们既没有为自己设置不幸,也不想把不幸带给他人。”因为人类敬畏和崇拜诸神就在于它们具有“神圣的完美性”,最后威莱乌斯得出结论,“神没有理由要去做事,它不会涉及任何活动,它也不从事任何劳作,它只为自己的智慧和神圣而感到喜悦,他拥有完美的确定性和永恒的福祉。”威莱乌斯没有否定诸神的存在,他把神性看成是完美的确定性和永恒的福祉,只不过它通过“先觉”刻进了人类的心灵,从而变成了人类建立在理性上的美德,也就是说,神性变成了人性,完美性变成了美德,而且诸神从不进行劳作、不涉及任何活动,他和自然以及人的世界是截然分开的,这似乎就是西塞罗关于神性的一种观点:诸神超然于世界之外,不照料和管理这个世界,而即使在人类世界有神存在,他也是和伊壁鸠鲁一样,是神圣的存在者。
对于威莱乌斯的观点,主人科塔给予了否定,他直接表示,“我根本不能接受这些观点”,他还是回到关于诸神的本性的主题,要回答诸神的本性这一问题,就必须回到更为起点的问题:诸神是否存在。“我暂且同意诸神是存在的。”科塔接着提出的问题其实依然是一个存在与否的问题,“那么请你告诉我它们来自何处,在哪里,它们的躯体、理智和生活方式是什么?”伊壁鸠鲁对于神具有的原子性说法,在科塔这里就被否定了,“首先,这些原子是不存在的。一个没有体积的事物就是虚无。其次,整个空间充满了物体,因此不可能存在虚空和个别的原子。”如果是原子构成的,那么诸神就不是永恒的,因为在原子构成之前,在神存在之前,就有一个没有诸神的时间;再者,如果诸神有一个开端,那么必将有一个终结,那么怎么会有基于神性之基石的永恒快乐呢?威莱乌斯说神有类似躯体和类似血液的东西,在科塔看来只不过是逃避这种两难处境的诡辩,“因此,伊壁鸠鲁的诸神必定只是似乎存在而实际上并不存在。”
伊壁鸠鲁学派最重要的观点就是诸神具有人的形式,科塔再次发问:诸神具有人的形象,是不是意味着我们的形象就是神?当人思考神的时候,因为“先觉”而使心灵具有固有倾向从而把神想象成人的形象,那么这种想象是理智的必然还是幸运的机遇?“多么幸运的一次原子碰撞,人竟然从中突然以神的形象出现了!”而且如果说神是人形之神,那么诸神是不是长得一模一样?如果不是那么谁比谁更美?谁才具有最完全的美?神的美德就是快乐,美德是一种活动,但是如果神不参与活动何来美德?没有美德又何来快乐?“请告诉我,你将给诸神吃什么、喝什么、什么样的颂歌和鲜花、什么样的触觉和味觉,从而使它们沉醉于快乐?”在一系列问题之后,科塔认为,“事实上,与神最接近的不是人的形象,而是人的美德。”但是,如果诸神只是享受快乐而无所事事,又何来完美本性?如果没有完美本性,我们为什么要给予他们尊敬?为什么要虔诚?要敬畏?“如果没有任何善可以归功于诸神,永远没有,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崇拜诸神呢?我不知道。”由此科塔对伊壁鸠鲁学派提出了批评,在他看来,他们通过剥夺诸神的德行和恩惠,从而把宗教从人的心灵中彻底根除了,最终,无人敢靠近神,也无神敢靠近人,“因为神不爱任何人,也不关心任何人。”
威莱乌斯提出了伊壁鸠鲁学派对神性的看法,科塔对此进行了辩驳,那么斯多亚学派又有怎样的神性观点?巴尔布斯作为罗马时代斯多亚学派的领袖,他认为关于神学问题可以分成四个部分:神圣的存在者是存在的,神具有它们的本性,神统治世界,神关心人类,这和科塔所说伊壁鸠鲁将神和人截然分开完全不同。对于诸神存在,巴尔布斯认为当我们仰望天空时久能感觉到诸神的存在;当事物出现之前会有预兆,这就是神的预言,也可以证明神的存在;还有温和的天气、丰硕的果实都是神的恩赐,即使雷电、暴风、骤雨、洪水、地震等天象和异象也证明神的存在;还有天体有规则的运行、日月星辰的变化、优美和有序,都证明这一切并非偶然性的产物;而人体拥有坚实的肌肉、维持着生命的呼吸,从水中获得滋润,从火中获得温暖,这些也都是神性的体现;还有更高级的是人类的理性,这种万物中最有价值的东西,也是诸神存在以及神性的体现。
诸神存在和神性其实是一个观点的两面,巴尔布斯由此得出结论,“所有这些都是因为宇宙各部分的和谐一致;而这种和谐如果不是受到一个无所不在的神灵的保护,那就是不可能的。”这一观点是不是就是莱布尼茨“前定和谐论”的来源?所以神性渗透并保护着整个宇宙,宇宙也必定是一个理性的存在者,“神与自然界必定是同一的,世上一切生命必定被包含在神的存在之中。”所以宇宙自身是神圣的,整体的宇宙是完善和完美的,它就是神意,一方面,“我的信念是,宇宙以及其中的一切都是由诸神的神意创造的,并且永远由神意统治。”另一方面,万物都服从自然法则,自然法则是万物的起源、种子和父亲,而万物依据自然法则力物形成了最佳的秩序,包括人的存在,“宇宙似乎就是诸神和人的共同的家园、共有的城市。只有他们才具有理性的力量,才能根据公正和法律生活。”
与伊壁鸠鲁学派的无神论截然不同,斯多亚学说体现的是泛神论,与伊壁鸠鲁学派所说的神不参与任何活动不同,斯多亚学派认为神就是宇宙的存在者,就是管理和统治着宇宙,就是维持着宇宙的和谐秩序。但是对于巴尔布斯的阐述,科塔再次进行了质问,“迄今为止,我还没有从你那儿听到什么能使我相信诸神存在的理由。”巴尔布斯说抬头仰望天穹会认识到了神的存在,但是科塔认为既然宇宙不是神,神只是居于宇宙之中,那么抬头仰望看到的星辰当然也不是神,它们是自然现象,而且自然现象的运行也不需要神的帮助,自然的和谐也不是神圣力量的作品,同样,理性、信念、希望、勇气、荣誉、胜利、拯救、和谐及其他,这些事物显然也不是神,如果用这些材料去研究神性,就会出现错误,“邪恶的力量也被归于诸神,从而使之成为宗教狂的崇拜对象。”
科塔的论述在原文中出现了缺损,接续部分科塔已经在谈论人类对理性的误用,在他看来,人类会利用理性来行善,但是这样的人非常少,更多的人则是用来作恶,这就说明诸神并没有要求任何人为善,既然诸神对理性之善采取了无奈甚至放弃的态度,那么理性也成为了恶行的基石、不公正的根源,“正如第欧根尼经常说的那样,恶人的昌盛和交好运彻底证明了诸神的力量是虚假的。”而且科塔认为,神不关心个体,不关心民族,不关心整个人类,“所以如果神表现出对整个人类的轻视,我们也大可不必惊奇。”在这里科塔不仅在驳斥巴尔布斯为代表的斯多亚学派的观点,甚至是在完全否定神性。面对科塔的观点,在场的卢齐利乌斯要“举起双手反击你”,“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不会放弃它们,否则我会因此而感到可耻。”当然面对卢齐利乌斯的战书,科塔也做好了准备,“我本人一直很想讨论我所论述的学说,而不是不假思索地宣告无用。因此我相信你会很容易战胜我的。”
但是这场讨论并没有在科塔和卢齐利乌斯之间展开,“讨论到此为止,我们都各抒己见。”西塞罗给这一讨论会画上了句号,这仓促的结果也证明西塞罗的这部著作更像是未竟之作。但是在让讨论会终结的同时,西塞罗对其中发言的几个人做了判断,“威莱乌斯认为科塔的论证最佳,而在我看来似乎巴尔布斯的观点更接近真理的影子。”这是西塞罗“到庭”、掂量证据然后作出了判决,但实际上他只是对讨论者的观点做了简单判断,而并没有真正发表自己的看法,而且在这场讨论会上,西塞罗自始至终都没有发表看法,就像他所说,“我只是作为一个听众,一个公正而毫无偏见的听众,没有义务勉强维护哪一种意见的真理性。”但是西塞罗并非只是完全的沉默者,他对讨论会的记录本身就是为了“公正而毫无偏见”,而他在最后认为巴尔布斯接近“真理的影子”,这也表达了他的观点:到庭就是为了掂量证据,掂量证据是为了作出判决,而作出判决的意义在西塞罗看来,就是要学会“批判”。他在《第一卷》中自述了对哲学的立场,判断不能草率行事,也不能不加批判地接受错误观点,更不能顽固坚持尚未充分讨论和理解的理论,“就我自己的立场来说,我想我会乐意看到真诚的批评,而对恶意诽谤严加驳斥。”
哲学需要再日常生活中体现,要让人民对哲学感兴趣,要积极推动哲学的拉丁化,这些都是西塞罗致力于学习哲学的目的,“世上万物有一种奇妙的连续性和发展,因此每一事物都与其他事物相关联,所有事物都联系在一起,就像一条长链。”但是在哲学的态度上,西塞罗认为,我们不应该集中在权威的分量上,而是集中在论证上,权威只是初学者的绊脚石,它会带来盲目和错误,而论证就如这场讨论会一样,各自阐述观点,也辩驳他人的观点,这就是批判。西塞罗之所以追随学园派,也正是这个原因,“学园派的哲学方法,亦即批判一切、不作任何肯定,是由苏格拉底引入的,阿尔凯西拉斯使之复活,而卡尔涅亚得斯使之巩固。”论证的价值就是“发现真理”,即“对现有一切哲学理论作出肯定或否定的论证”,当然西塞罗的论证也表达着自己的观点,一方面,他抱着学园派怀疑主义的态度对以往的神学观点进行研究,尤其对传统的以神人同形同住论为特征的希腊罗马宗教进行批判,另一方面,他又站在有神论的立场上,批评以伊壁鸠鲁学派为主的无神论思想,也正因为此,西塞罗的沉默其实就是在言说,因为他从批判伊壁鸠鲁学派的巴尔布斯身上看到了“真理的影子”。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56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