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09-29【“百人千影”笔记】安德烈·祖拉斯基:“银色星球”上的迷恋和迷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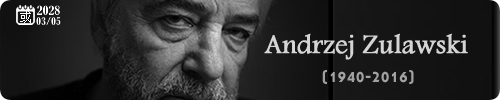
电影就是小偷,是经过化学反应形成一种怪异的叠加:它本身是戏剧,但是通过摄影机等干预手段,成了电影。
——安德烈·祖拉斯基
我承认,对安德烈·祖拉斯基的了解在“百人千影”之前是一个空白:完全不清楚他的电影和波兰当局形成的紧张关系,不知道《着魔》世界里创造了何种突破感官底线的影像,未知于最具野心的《银色星球》如何会是“一部拍给另一个世界的人看的电影”,当然,更不知道和苏菲·玛索之间有过长达15年的情感纠葛……无知或者未知,而当从零起点进入到安德烈·祖拉斯基的世界,当不带固化的观念闯入陌生的影像,是被扑面而来非常规的叙事所迷惑?还是回归于理性安然从那个世界退出?
在打开祖拉斯基所有被下载的电影资源之前,没有过这个疑问,观看只是观看,影像只是影像,彼此都是一种独立的存在,在作者和观者可能的关系里,最后一定是打开后的关闭,开始后的结束,甚至只是“百人千影”中一个停留过的点而已。但是在几乎看完了祖拉斯基的所有电影之后,观看和被观看之间的物理关系慢慢附上了一层起反映的化学物质,即使它最后回归于彼此独立的世界,也至少在燃烧中留下了一些刺鼻的味道,甚至还能找到灰烬的存在。实际上,祖拉斯基构建的世界就是为观者的阐释保留了位置,镜头的多义性,叙事的开放性,风格的诡异性,都在允许着他者的进入,那个进口永远放置在那里——这也正是他进入电影世界所看见的一切,“我的生命由文学、绘画、音乐交织而成。这得继于我的家庭,也来自我一生的故事。”
或者这就是创作和阐释可能同一性的最基本要素,而他对电影艺术本质上的阐述就是一种进入的姿态:从戏剧到电影,不只是形式上的改变,而是一种化学反应,是“怪异的叠加”,当它在摄影机的干预下而变成“电影”,这个过程是拙劣的,是非常态的;但是,电影是为了它自身的存在,当它从绘画、文学、音乐、杂耍、哑剧从窃取或者借鉴了形式和内容,作为“小偷”的电影是丰富了自己,成为了另一个自己:“所以要我说,电影就是个杂种!也正因为这一点,我爱电影。”从怪异的叠加到丰富了自己,从小偷到杂种,从非常态的观望到“我爱电影”的抒情,祖拉斯基就是完成了一种进入:从观者而成为作者,是作者面向所有的观者。但是,对于祖拉斯基来说,成为作者面向所有的观者,并不都是一种开放性,面向观者也不是“面对观者”,至少在他那里这是一个自觉而不自为的过程,也正是从面向到面对,从本身开放到为了开放,祖拉斯基最后走入了两条路:“我爱电影”在爱的意义上是开放的,是自觉地开放,它是一种迷恋式的构建,让所有观者都能进来;但是当“我爱电影”在“我”的意义上阐述,则变成了一种自我迷失,他反而拒绝观者进入,从而关上了那扇门——从我“爱”电影的迷恋,到“我”爱电影的迷失,在祖拉斯基的影像里,就是两个关键词:一个是:魔,一个是:欲。
“我去了西伯利亚,去了非洲,也去了加勒比海,我见过巫毒作术,也看过萨满释法,他们真是全世界最好的演员。”演员的身份和电影的本质是一种完美的契合,“正如柏拉图的洞穴寓言所示,表演才是人类的常态。我们为什么会想要表演?我不知道。就像小孩为什么喜欢玩耍,我也说不上来。这是我们根深蒂固的本性。”所以祖拉斯基是在挖掘人类的常态,人类的本性,当他把这一切的表演都纳入到“怪异的叠加”之电影中的时候,对常态和本性的挖掘便从形式意义进入到精神意义,而“魔”便是那个最深刻的存在——以“魔”的方式串联起祖拉斯基对常态和人性的挖掘的电影,是这样一个影像的链条:从第一部电影《夜的第三章》到《恶魔》,再从《恶魔》到《着魔》,然后是《银色星球》,然后是《萨满教的迷恋》——以黑暗之夜开局到迷恋的悲剧为结,在这个“魔”的世界里,祖拉斯基如何构建一个指向人性本质的开放世界?
对线性时间的无情打破,当然是祖拉斯基在处女作《夜的第三章》中的野心和实践:从一开始,祖拉斯基构建的是一个完全是传统叙事的结构类型,但是在时长三分之一处,这种线性叙事被完全打破,在场景的转换中,主人公米高既成为目睹海伦娜生下孩子的旁观者,又成为了自己孩子卢卡斯的父亲,还成为了看见了刚生下孩子的家庭的保险工作人员,在镜头的魔术里,出现的是三个父亲,也出现了三个海伦娜,而米高既是父亲也成为了观者,米高目睹了自己的过去,目睹了海伦娜和自己的过去生活,时间回来了,自己回来了,但是这一种回来却让米高带着巨大的不安,他诅咒上帝让一切的真相重现,似乎自己曾经的所作所为是罪恶的——祖拉斯基似乎就是从这里开始,不断地制造新的时空,从而揭开了那个所作所为的世界。这是一个看见的叙事,它抛弃了客观镜头,抛弃了线性叙事,因为看见本身就是主观的,当然也是开放的。
这是祖拉斯基的叙事实验,这是祖拉斯基设置的看见寓言,而三分之处的起始也成为关于“魔”的进口:四位天使吹响号角,世界走向了末日般的存在,世界的三分之一被摧毁,海水的三分之一变成了血,大海里的生物死了三分之一,海上航行的船只三分之一被烧毁,太阳的三分之一、月亮的三分之一、星辰的三分之一渡边的灰暗——三分之一的灾难指向了末日,电影三分之一处的进口无疑也是末日的一种书写,祖拉斯基所阐释的主题,就是世界存在的罪恶:当海伦娜、卢卡斯和自己的母亲被杀死,面对三具尸体,米高控诉着:“上帝啊,是你没有引导我们。上帝啊,是您允许脆弱的人被杀害并制造怨恨。上帝啊,是您允许残酷的繁殖让人类互相残害。上帝啊,是您让最邪恶的势力上台,并交给他们鞭子。残忍的上帝啊,您对我们毫无仁慈之心。”上帝变成一种残忍的存在,上帝本身就带着罪;在米高去修道院看望奥列克的母亲时,他遇到了修女克拉拉,克拉拉对米高说出了“奥秘”,这是关于妓女的奥秘,这个奥秘的核心就是亵渎,对善的亵渎,对信仰的亵渎,对爱的亵渎;蒙着脸的罗真克兰找到米高,说自己害怕见到自己的脸,然后他给了米高一本启示录,米高念出了启示录里的话,启示录说到了魔鬼,说到了撒旦,当米高读完这段话,他看见了走出去的罗真克兰在门口被纳粹枪杀……
虽然祖拉斯基在阐释这个末日世界的时候,大段大段引用文本的句子,抛弃更开放的镜头语言而以文字解读,当然是一种偏执,有些也用力过猛。但是,祖拉斯基用实验的影像构造了末世的迷宫,把所有的苦难和死亡都装入其中,让自己看见,也让自己被看见,看见是一个寓言,看见是一个预言:这是一个撒旦诱惑人类的时代,这是一个暴力横行的时代,这是一个处处存在吸血虱子的时代。《夜的第三章》是祖拉斯基关于“魔”的起点,同年的《恶魔》,在主题的指向性上和《夜的第三章》异曲同工,但是祖拉斯基加入了更多实验元素,对“魔”的阐述也更具社会性。《恶魔》这一片名就是祖拉斯基对这个世界之存在的命名,雅各布刺杀国王成为了谋杀者,这是对国家之恶的见证;而国家之恶又延伸到了个体人性之恶上,皇家舞会、国家婚礼、国王剧团都带着浓厚的国家主义;从未婚妻开始,到父亲、妹妹、艾赛因和母亲,在道德层面上呈现出恶——无论在国家层面还是在个体道德层面,雅各布都看到了让人无法忍受的罪恶,这是双重的恶魔般存在。
这是“魔”的客观存在,但是面对这种罪恶,雅各布的身份开始了另一种转变,就像他的革命宣言所说,必须用武力创造平等,而武力意味着暴力,意味着杀戮,那么在这个意义上,他从恶的见证者变成了恶的实施者:他第一个杀死的人是在母亲那里的女人,女人被关在笼子里,作为一种“卖淫”的存在,他杀死了她,似乎在控诉着母亲的罪行;之后雅各布拿着锋利的刮胡刀,杀死了剧团里的男演员和土耳其女人,还杀死了想要鸡奸他的团长赫兹,这是对恶的艺术的谋杀;之后,他又在大使的晚宴上杀死了艾赛因,而那时拥有很多钱的母亲也死了,虽然不是雅各布所杀,但是死亡意味着对恶的摧毁,他还烧毁了那面旗帜,烧掉了房子,甚至他还用手中的刮胡刀杀死了那匹马……死亡已经发生,死亡正在发生,死亡将要发生,雅各布用武力杀死了那些制造罪恶、带着罪恶的人,“所有的罪恶必须被惩罚……”这就是雅各布的人生信条,但是,在毁灭了恶的同时,他也制造了恶,实施了恶。
资本家和人民平等了吗?国界恢复了吗?共和国找到了它的荣耀?没有,一切都没有实现,。所以,在祖拉斯基摇晃不稳的手持镜头里,在疯癫版地叫喊和抽搐中,在疯子般的屠戮中,在背叛和乱伦、革命和反革命的交错中,上帝就是带着恶魔的面具惩罚着人类,原因和结果的混杂,恶魔和上帝的混杂,那么革命有时就是反革命,罪犯有时候就成为了救赎者——被神秘人命名为“神”的雅各布就是一个混杂的存在,而作出命名的神秘人更是背后掌控着这个末日世界——国家、革命、国王,祖拉斯基赋予了“魔”社会性的特点,这是一种对《夜的第三种》用力过猛的某种纠正,而1981年的《着魔》以更现实和更隐喻的方式展开另一个“着魔”的世界。
片名:Possession,又名“迷恋”,电影类型:剧情/恐怖。这是关于《着魔》最初始的标签,也是一种外在性的标记,但是这个关于着魔的故事完全可以从这些符码进入:当“着魔”的故事发生,当“入迷”的情节展开,谁是施事者?谁是受事者,或者说,谁是“着魔”的主体,谁又是“入迷”的客体?主客体之间的关系缝合,才能使事件发生,但是这个统一体似乎天然地具有二元论的特点,它们在电影中最常见的表现形式便是男/女,对应于角色则是“马克/安娜”:或者是马克对安娜着魔,或者是安娜对马克入迷,也正是这种最基本的二元论解析,对应于剧情类型,就是那个斜线符号的存在:这是剧情片还是恐怖片?如果抛弃简单的二元论,斜线或者变成了一种渗透式的存在:从剧情片变成了恐怖片,从恐怖片或者可以回归剧情片,于是,回到马克/安娜的“男/女”主客体关系,电影走向的是一种映射的复杂关系,“它是表示删除的斜线,镜子的表面,幻觉的墙,对照的边界,界线的抽象,能指的倾斜性,纵聚合体的定位标志,因而亦是意义的诸如此类。”
一直到怪物出现,之前的所有情节都是一部家庭伦理剧,马克和安娜的情感危机引出的是背叛、出轨和爱的可持续问题,但是当怪物出现,惊悚弥漫,着魔式的叙事成为祖拉斯基对人性寓言的最深刻剖析:安娜的出轨,安娜的不忠,安娜的离开,都变成了马克的妄想,这种妄想症才是他着魔的真正原因,“上帝对我来说是一种疾病。”这是对病态自己的注解,上帝没有了,信仰不见了,当然爱也变成了怀疑,变成了恐惧,“也许我们可以通过疾病接近上帝。”以病态的方式接近上帝,那么上帝也变成了恶魔:和安娜做爱的怪物,和安娜一起杀人的恶魔,难道不正是马克想象的一种存在?从现象界进入想象界,最后进入象征界:魔鬼是他人身上的魔鬼,也是自己创造的魔鬼,魔鬼杀死了人,魔鬼当然也杀死了自己,末日真的就降临了:防空警报被拉响,飞机在轰鸣,爆炸声传来,这是战争毁灭的信号,终于魔鬼统治了这一切。
《夜的第三章》里,因为上帝的残忍而打开了魔的世界,《恶魔》里,因为上帝戴上了恶魔的面具而惩罚人类,《着魔》里,则是魔鬼创造了既是上帝也是魔鬼的自己,而在1988年的《银色星球》里,祖拉斯基以更迷幻、更宏大、更多元的方式,让“一部拍给另一个世界的人看的电影”成为永远让人类自己看到丑陋、集权、罪恶的启示录。根据叔父的小说《月球三部曲》改编,披上科幻的外衣,祖拉斯基只是以一个外域的视角来重新审视人类之“着魔”。“天父给了每个人种子,让我们自己在身体里成长,是植物的种子就会成为植物,是动物的种子就会成为动物,理性的种子会成为神学家,智性的种子就是天使或上帝之子……”在飞船抵达银色星球的时候,幸存者发出了人类之声,人类的命运是被种子主宰的,而种子观所强调的天父是一种信仰,但是人类的信仰何为?在宇航员莫名死亡,在对银色星球一无所知的情况下,重要的不是信仰,是生命。所以,此时谈论信仰仿佛就是一种愚昧,只有生命才是最重要的,也由此,人类开始了从信仰到生命的蜕变,新的星球,新的生活,新的历史从此开始,在这个意义上,“进入”之前的人类,以及“进入”初期对信仰的谈论,只不过是一段“前历史”,只有在这里开始了生命的新阶段,才是历史真正的开启。
当仅剩的宇航员开始在星球上繁衍,人类重新进入了原始社会,而且是一个女人作为繁衍之母的母系社会,建立了社会,接着便是向外的拓展,大海成为另一种信仰,但是铩羽而归是这个信仰的失落,也正式从这个意义上,祖拉斯基选择了一种捷径,他让马克乘坐另一艘飞船抵达了银色星球,并在被大家尊称为“老头子”的权威者面前降落,于是马克变成了“新神”,由此开启了银色星球的神时代。在造神中被封神的马克也自认为是神,在神的世界里他的一切欲望都被满足,但是这完全是一个被异化的神,他只是普通的人类,当马克制定的征服计划失败,当马克在众人面前让他们归顺自己,最后忍无可忍的人群将他也钉上了十字架,“我是神”成为他垂下头之前的最后一句话,而实际上被神化的他连“我是谁”都没有找到最终的答案,而这是不是人类文明必然经历的阶段?而最后进入的是人类难以逃离自身束缚的人时代,以宇航员杰克为代表的人类开始以回归的方式寻找信仰,但是很明显,杰克就生活在自己成为“外星人”的世界中,他面临的是被驯化或被清除的命运,他以为的爱也只是一种阴谋,那一刻杰克的确看到了人类的罪恶,而祖拉斯基在这里完成了一次穿越,他让杰克来到了马克死去的地方,这是一种对他人之死的看见,也是对人类之罪看见,“我们都是有罪的。”
祖拉斯基在《银色星球》中构筑了从地球文明进入银色星球的原始时代,造神运动开始之后的神时代和人类发现自身之罪的人时代,三个时代都是人类“着魔”的悲剧,“一部拍给另一个世界的人看的电影”成为祖拉斯基最具野心的一次实验。但是在主题之外,祖拉斯基的遭遇反而变成了对现实之恶的注解,它在文本之外大大丰富了“着魔”的象征意义:1977年《银色地球》拍摄完成八成素材之后,新上任的波兰文化助理大臣下了禁令,销毁了场景、布置和服装。“您所观看的这部影片摄制于10年之前,这是一部遗失了五分之一的不完整的电影,而我们也不会再重拍那些被毁的部分,在影像遗失之处,我会奉上旁白对这些缺失部分进行描述。”遗失的素材变成了文字,文字旁白的画面是波兰街头的场景,跨越十年的“合成”自然成为了另一部电影,而在这另一部电影里,祖拉斯基也成为了电影人物:街头的橱窗玻璃前站着一个男人,男人像是在祈祷什么,最后的一句话是:“我是安德烈·祖拉斯基,《银色星球》的导演。”
祖拉斯基在自己的电影中说着自己的电影,嵌套式的结构让他成为了电影的主角,而这种镜像般的存在为电影做出了最后的注解:“我能完成这部电影要归功于他们,同时本片完成过程中小小的戏剧性的一幕,与我们生命本身那伟大充满希望的庄严的戏剧性会继续不断交织在一起,就如同成功和失败相互镶嵌成的马赛克。”《银色星球》就是祖拉斯基表现生命本身伟大的庄严的戏剧性的一次实践,揭开了人类对权力、对自身、对欲望的“着魔”之恶。而八年之后的《萨满教的迷恋》,更以大尺度的感官刺激书写了“着魔的邪恶本性:“意大利妞”打死了心爱的米切尔,蚕食了流出来的脑浆,完成了关于欲望最恶心的命名,而最为可怕的是,她竟然像什么事也没有离开了现场。“意大利妞”的占有,米切尔的死,构成了关于爱欲之死的一个标本,而这个标本对应于那具被挖出来的萨满教巫师之标本,便是历史的再现,便是宗教的再现,便是扭曲的情爱的再现,甚至是欲望机器的再现——这个再现在米切尔那里是发掘,在“意大利妞”那里是重现,而当这具2500年前的黄教僧的干尸成为现代情欲世界的写照,“萨满教的迷恋”指向的不是宗教之研究,而是人类自我的迷失。
因为迷恋而迷失,这本是祖拉斯基对“魔”世界的一种解读,一次警告,“耻辱,这是没落的黄昏……”的确,在祖拉斯基构筑的“魔”世界里,道德的规则被解构,传统的叙事被颠覆,甚至病态成为一种常态,这其实也是祖拉斯基自己的“着魔”,它指向的是人类的堕落。但是在祖拉斯基表现“爱”的电影中,迷恋而迷失完全呈现为一种粗浅的、拙劣的书写,如果说对“魔”的叙事是开放的、残忍的、具有野心的,那么对“爱”的解读则是封闭的、混乱的、留存于感官的。《爱是最重要的事》、《没有私生活的女人》、《狂野的爱》和《我的夜晚比你的白天更美》构成了祖拉斯基“爱”的文本,在这些文本里看不到真正的爱,只有没完没了的性,只有无处不在的欲,只有裸露的身体,刺激的感官,甚至几部电影的基本模式也雷同于一种不对称的三角恋。
《爱是最重要的事》中,祖拉斯基的确用“我爱你”的结构构筑了主题,但是在什么是真正的爱的阐述中,在情节的快速变化中,在人物捉摸不定的性格里,祖拉斯基反而把爱推向了一种纯粹剧情化的游戏中,谁爱谁,谁不爱谁,似乎都是表象的,随机的,那种爱也像是悬空在那里,只是成为他们口中的一个词,成为了电影的一个片名。《没有私生活的女人》又名《公共女人》,政治生活中伊黛尔的爱被湮没了,电影世界里伊黛尔的爱死了,这就是没有隐私的隐喻,在“戏中戏”的结构中,女人既在祖拉斯基所叙述的电影故事里成为被取消了隐私的公共人物,又在打破了第四堵墙的间离效果中,让他镜头下的女人一览无余,这种残忍正如伊黛尔对导演卢卡的评价一样:“你爱倒行逆施,拍戏如此,生活也是如此……”《狂野的爱》完全是狂野而没有爱,当所谓的爱被置于狂野的环境里,失去了真正的意义,暴力不断发生,死亡不断发生,疯狂不断发生,情节散乱了,逻辑湮没了,所有的行为都变成了荒诞,变成了戏谑;《我的夜晚比你的白天更美》中的爱更是一种悬空的存在,将死的男人和留下童年阴影的女人,完全以虚构的方式进入到自己的夜晚,“游泳的鱼”最后变成了被淹死的鱼,在俗套的故事里让生命走向了终点,也让祖拉斯基的“爱”走向了终点。
祖拉斯基为什么能构建一个颇具野心的“魔”世界,却在“爱”中迷失了自己?也许祖拉斯基本身就是一个无视任何规则的魔鬼,本身就在开放的世界里允许自己进入,本身就洞悉了人性之恶的多面体,但是当迷恋成为吸食脑浆的感官刺激,“爱”本身就成为了一个道具,祖拉斯基看见的也许真的只有身体、肉体,真的面对的是欲望的结合体,“我认为被爱慕或敬畏的时候,人体就是艺术,而这种艺术是不该被遮挡的。”爱成为了欲望,情变成了肉体,电影的大门已经关上:只有符号,只有能指,世界就是祖拉斯基最后一部电影《黑暗宇宙》:祖拉斯基没有在小说原著的晦涩中构建一个多元性的宇宙,反而迷失于一种影像的符号堆砌,托尔斯泰、司汤达、奥登的文学符号,萨特的哲学术语,帕索里尼、《星球大战》的电影注解,似乎也都变成了外化的文本,并没有融入到电影中成为一种指涉,过度和匮乏叠合的影像世界,一切的宇宙仅仅是一个庞大的外壳,最后字幕后的彩蛋就像是对符号所指的彻底解构:蜥蜴,吊死的猫,蛤蟆,它们只是一堆道具,就像蕾娜问的那个问题:“你能让我成为一个好演员吗?”在一堆道具面前已经毫无意义。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76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