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03-30《“景观”文学》:拒绝主观性的消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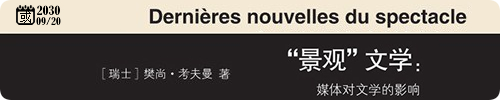
虚构,它是由严肃真实的事件和事实组成的:如果我们希望的话,就是自我虚构。它将一种冒险的语言托付给一种自由语言的冒险。
——《“我”不再让人憎恶》
一段话,写在一本书的封底,它第一次对“自我虚构”进行了定义,也清晰地区别了自传和“自我虚构”的不同:自传是为伟人而准备的,自传是“为其生命中的星夜、为其优美的文体”而准备的,而自我虚构是将冒险的语言变成了语言的冒险,语言在明哲之外,在传统之外,在小说的体系之外,它由汇聚、串词、叠韵、谐音、非谐音以及“文学之前或之后”的具体书写所组成。
这是塞尔日·杜布洛夫斯基在1977年提出的定义,它就写在小说《儿子》的封底。一本1977年的小说,还是一部创作的小说,一本由作者创作风险给读者的小说,但是当杜布洛夫斯基以如此方式区别了自传和自我虚构,作者指向的“我”是不是发生了本质的变化?自传和伟人有关,和伟人生命的星夜有关,和文本所体现的优美文体有关,或者说,自传就是一种对权威的书写,而自传本身在书写层面上也变成了权威。但是自我虚构所突出的是“虚构”,是自我沉浸在虚构中的表达,它体现的是语言的冒险,在串词、叠韵、谐音、非谐音的语言冒险中,在和伟人无关的虚构中,它已经将事实变成了一种杜撰,按照樊尚·考夫曼的说法:“它是一种有意识的随心所欲,或一种虚假式的体裁。”甚至,它在取消了权威性之后,小说成为了“人人都可以涉足”的文本,粗糙、实在、露骨、过激、不崇高、无审美的风格也标志着“作者非专业化”的开始。
作者还是作者,书还是书,从自传到自我虚构,到底经历了什么?考夫曼引用杜布洛夫斯基的例子只是在说明一个问题:作者被景观化了,自我虚构便是景观化的征象——自我虚构变成了语言的冒险,它不再继承传统小说的特点;小说的虚构变成了随心所欲的杜撰,所谓的事实也成为了一种虚构;作者沉浸在自我虚构中,他不再是真正的作者,权威性不复存在,或称之为“作者之死”……在作者景观化、小说成为人人涉足的文本变化中,为什么会有“作者之死”?作者之死是作者的原因还是社会的原因?作者之死带来的文学嬗变是一种对时代的适应还是一种历史的倒退?专业、权威的话语秩序还能恢复吗?
“作者之死”不再只是一种现象,已经成为了一种本质反映,曾经罗兰·巴特宣布了“作者之死”,这是针对作者在读者面前消失这一文学境遇而言的,米歇尔 福柯则将作者分解为不同的“功能”,莫里斯·布朗肖则说到了自己消失,更早的则是马拉美,他让诗人的存在变得毫无意义。“作者之死”在文学、哲学意义上并不是一种颓败之死,甚至于要获得“作者之死”的权力,必须以生命为代价,按照乔治·巴塔耶的说法,宣布自我死亡必须用神圣来装点自己,甚至“死亡”是一种对习以为常的标准化或平凡化的抵抗,“只有最伟大的作家才有能力死去。”在这个意义上,“作者之死”也构成了对伟人准备的自转的一部分。但是在现在的时代,作者不是死于肺结核、疯癫、酗酒,不是在对平凡化进行抵抗,不是用神圣来装点自己,更不是自传的一部分,而是作者之我变成了别人,这个别人就是景观化的作者。
“景观”是居伊·德波提出来的一个概念,他将其发展成了自己的一种批判思想,考夫曼也在对居伊·德波的思想考察中审视了“景观”,而现在,考夫曼认为德波的这个词正好可以形容目前“作者之死”的现实,与其说这是对文学本身的考量,不如说直接指向了景观化之外在的“景观”,即“媒体对文学的影响”。在序言中考夫曼引用了一种叫“加拿大姜汁汽水”的东西,在法国它被人们津津乐道的广告语是:“姜汁汽水的金黄色就像啤酒,它的名字听上去也像啤酒……可它不是啤酒。”流转的广告语背后揭示的是这样先是:它的外表可以以假乱真,但不是货真价实,姜汁汽水文凭、姜汁汽水合同、姜汁汽水科学研究,以及还有姜汁汽水作者和文本——它们都成为了景观化的丰富呈现。所以从“加拿大姜汁汽水”考察景观化的呈现,考夫曼在“序言”中一针见血指出了这一现场的根本:这是在“注意力经济体制”下的一种必然,作者在“公务化”中变成了别人,作者-功能成为了在数码等媒体秩序中被“配置”的存在,书写变成了“看见”,“从一个适宜写作的年代,变成了一个只用眼睛为所能看而看的时代;变成了一个只用眼睛为看到而看的时代;变成了一个只看名人的时代。”最后,那些著作就变成了在电视、互联网上被介绍、被消费的“闲书”,它就像一次性餐巾纸一样,被扔进垃圾桶的时候发出“哐当”的声响,而这声响就具象为社交媒体上向上或向下的大拇指、表情、感叹词、我赞、我踩、我分享的符号。
“媒体对文学的影响”,顾名思义,是媒体首先让作者之死发生,是媒体率先景观化,“媒体即讯息”这一经典定义的背后是:一个媒体就是一个生态系统,一种媒体展示其讯息和交流的技术中,也执行着它的统治权。考夫曼梳理了媒体发展的历史,起先是文字域的书写,这个历史时期也称为了“逻各斯域”,之后印刷术的发展,图书得以出版,这就进入了“印刷书写域”,然后电视的发展,又进入到了“视听图像域”,而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数字“超媒体域”应运而生。这条历史发展轴线,是媒体发展变化也是媒体统治权迭代的历史,而进入数字超媒体域的时代,配置便产生了,它不仅在外部权威、内部权威上进行配置,还在市场权威中进行配置——尤其是网民参与的互动中,数码技术为特征的web2.0本身也成为了一种配置,所以出现了自助出版、众包、众筹融资等形式。在这样的现实中,数字媒体用权力消除了所有距离和中介,它让文学变成一种即时性的存在;没有人再去关心书籍文化和“作者-功能”。
从文字、印刷、视听和数字媒体,迭代本身就是媒体边缘效应的一种体现,它是媒体之间不断相互作用的结果。但是同时,在景观表现上,也呈现出一种“丰富”的变化,这种丰富变化的核心其实回归到居伊·德波的“景观社会”:这是一个对被驯服社会的描述,这是一个对被异化的社会的概述,这是一个被商品拜物教统治时代的定义,而现在,景观化就只有一个标准:被关注,它是注意力经济的体现,它为公众关注度代言,“景观之所以存在,不仅仅是为了让大家成为鲁莽而幸福的消费者,也是为了让大家成为注意力经济体制下的参与者、商品和对象。”似乎有一种观点认为,在网络时代恰恰意味着我们可以摆脱景观摆脱强制权,因为网络实现的是民主式参与,是自由发言,是自我表达,甚至是自我塑造,在民主、自由的网络社会中,我们完全摆脱了旧式的“话语秩序”。但是,考夫曼一针见血地指出,所谓自由是让我们变成了数码文盲,所谓民主其实是非专业化的体现,所谓的自我表达就是“自我虚构”,而所谓的话语秩序更是新的独裁统治和市场配置。
| 编号:H21·2231212·2044 |
考夫曼从景观社会入手,分析了注意力经济、公众关注度等特征:注意力经济,就是将“注意力”兑换成为货币的一种体制;公众关注度所关注的不是事件而是人,是建立在不平等关系上、由无数的“观众”关注而产生的少数幸运儿;公众关注度体现的是价值,甚至是价格,将注意力经济的货币发展为资本,而这个象征性资本的付款者就是我们,这就成为了这个时代的“景观”。而在具体景观的生产过程中,还有很多的语法规则,它决定着如何对作者进行“配置”。考夫曼总结认为,景观可以被定义为出庭式文化、坦白式文化、真实性文化、透明度文化、牺牲性文化等几个维度:在景观中你必须出庭,出庭不是因为犯了罪,而是为了在景观里求得一席之地,拇指朝上、朝下、我踩、我赞这些都最后成为了出庭式文化的最后“判决”;坦白式文化和出庭式文化相辅相成,坦白就是将隐私公之于众,坦白就是将身体展露无遗,坦白就是让景观变得更为完善;景观需要真实性,就是要“眼见为实”,只有亲眼看见才会相信,于是出卖自己、揭露隐私、承蒙羞辱、遭受打击都变成了“真实”的一部分,变成独一无二的真实故事,但是在景观中,真实性只是一件外衣,它恰恰掩盖了自己的真实面目;这也是透明度的要求,只有一个变得透明才会吸引人的目光,才会赢得公众关注度,而透明最后演变为兽性、残暴和残酷;牺牲性是另一种景观表达,它以出卖自己、牺牲自己为表现形式,它完成的不是虚构而是再现,“一种们应该相信,而且我们不得不信的再现。”
这些景观的语法规则无非是同语反复,它是为作者配置的端口,而当作者从这些端口进入媒体,那么真正的文学上的景观就产生了:作者放弃了专业性和权威性,作者不再遵从书写的话语秩序,作者的写作的“灵晕”陨落,于是,作者开始了杜布洛夫斯基所说的“自我虚构”,他将书写变成语言的冒险,他创造了随心所欲的意识,他在编造杜撰的权力中游荡,他完成的是人人可涉足的文体——他就是“加拿大姜汁汽水”的作者。考夫曼利用“影像定格”的方式,分析了几位有代表性作者的景观化写作。杜布洛夫斯基第一个定义了“自我虚构”,他也完成了自我虚构的小说,其中有一本叫《夭折之书》,他在小说中让自己的妻子出场,让自己说话,并且对妻子恶语中伤,妻子是其中的人物,也是小说作者的合伙人;而除了小说“自我虚构”之外,杜布洛夫斯基还走进了电视节目《责问》,讲述自己新作《夭折之书》的创作过程,“杜布洛夫斯基在镜头面前是如此哀愁,如此消沉,而我们却并不太清楚他是否因撰写此书而感到后悔,还是因某些观众会将他看作杀人凶手而苦恼,我们更不知道他是否因死去的妻子过早抛弃他而责怪她。”但是这已经构成了“景观”,不管是杜布洛夫斯基在小说中逼妻子走上绝路,还是在电视节目中摆出有罪的样子,都是对景观语法规则的一次运用,是出庭,是坦白,是牺牲,更是为了注意力经济和公众关注度。
吉贝尔用自己的三部曲曝光了自己痛苦垂死的身体,克里斯蒂娜·安戈书写了乱伦的生活主题,同样的,他们也在电视访谈节目中面对观众进行了出庭、坦白、牺牲,制造了注意力经济,也获得了公众关注度。但是在“影像定格”中,考夫曼选择对安妮·埃尔诺的小说进行考察,他以“被割的孩子”定义安妮·埃尔诺的创作:2003年,安妮·埃尔诺发表了与弗雷德里克·伊夫·詹内特的长篇访谈《文字如同一把刀》,书名就指向了安妮·埃尔诺的牺牲和神圣:文字是自我伤害的工具,是忍受痛楚的工具,也是制造痛楚的工具,安妮·埃尔诺在访谈中认为,她所写的不是“虚构”,也不是“自我虚构”,而是真实的、确凿的东西,是完全科学的、社会学、普世的,“玛格丽特·杜拉斯虚构了她的生活,我则相反,拒绝所有虚构。”对拒绝虚构的安妮·埃尔诺的关注,在考夫曼看来,其实提供了一种混杂性,一方面,安妮·埃尔诺说自己不是虚构与自我虚构,她一刀一刀所割出来的都是真相,这是对真实性的抵达,但是她将这些真实的隐私写进小说里,是面对自己的表现,甚至是面对自己的耻辱,它构成的创伤性文学是不是也是一种自我牺牲?也是在书写和出版甚至访谈中完成了出庭、坦白?
安妮·埃尔诺的含混性在考夫曼看来,具有的特殊意义是:她不是虚构了这种为了公众关注和注意力经济的故事,它已经发生,我已经有罪,所以我写作,所以我对真实写作,“我面对自己、反对自己、反对他们,因为我所写的,是绝对耻辱的,所以也是绝对真实的。”写作反而变成了一种赎罪和免罪,所以考夫曼认为,安妮·埃尔诺的牺牲和他人的不同,“不管怎么说,安妮·艾诺赋予了景观作家一丝贵族气息。”这种贵族气息让安妮·埃尔诺的书在考夫曼看来还是一种著作而不是随时可以扔掉的闲书。但仅此一例,在对作家进行“影响定格”而分析了作者景观化的表现之外,考夫曼又从作者转向了景观化文本,《坏小子库默尔》是2010年问世的一部片子,讲述了瑞士记者汤姆·库默尔奇特的工作方式,他住在好莱坞,为了给瑞士和德国地方性报纸撰文,他采访了众多明星,主打的是原创性和真实性,但是很多年之后人们才发现,访谈内容完全是文本的抄袭,很多访谈还是被捏造出来的。库默尔身为记者,以抄袭和杜撰的方式书写真实的新闻,这当然是对新闻的一种可耻违背,但是他的这种做法背后依然还是景观的权力在发挥作用,而记者也是作者,在没有原创性和“灵晕”艺术的时代,所有作者都是库默尔,“我们越是生活在一个充斥着无穷复制的世界里,我们越是会对‘真实性’如痴如醉,而且我们还要求文化产业在各种领域里向我们提供‘真实性’。”不仅仅是文学创作,学术研究在景观化中也变成了标注文献出处等丧失了原创性的行为,“我们只需大致掌握改写、意译和迂回的艺术,并通过增加注脚数量的办法来获得一张可以证明‘真实可靠’的证书。”
不管是记者还是论文研究者,作者之死都变成了景观化的一种常态,而在作者之死中,“群体的智慧”变成了新的景观:在各种论坛和会议中,网民成为了“文学规定者”,组织机构成为了作者,众包和众筹等模式出现,而真正的个体彻底消失,这就是考夫曼所说的作者第二次死亡,“作者就在您身边,他回应您,不仅仅当住在隔壁的您,潜入他家问他要盐,或者拽着他闲聊他的最新作品,而且当您近身贴着他的肩膀,向他提出您的看法,给他建议时,他也回应您。”网民成为了作者,知识被共享,不再有文学流派,不再有文学史。作者的命运是:“要么死里逃生,要么因被网民淹没而消失”。
从景观化的现象到语法规则,从访谈节目到互联网网民,它们共同制造了“作者之死”,它们一起完成了“作者景观化”的社会。但是回到起点,考夫曼的问题是:为什么创作和阅读会消失?他引用的是特吕弗改编的电影《华氏451度》中的情节:一旦发现书,就要将其焚烧,将持书者囚禁,而正确的方式是坐在电视机前观看电视节目。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节?考夫曼的回答是:因为书籍是造成不平等的因素,是差异化的原因,因为阅读可以让我变成独立的个体,我是平均主义的敌人。焚毁图书而让他们观看电视节目,这就是景观化的一个隐喻,也正是从这个情节入手,在大量分析了景观化现象之后,考夫曼认为,要抵抗景观化,就需要反其道而行之,也就是要恢复主观性,“我们的主观性是通过特定的书写和阅读培养出来的,这样想,是不是一种虚幻?是不是一种信仰?如果写作和阅读消失,我们的主观性是否也随之消失?”
这就是考夫曼在景观社会中寻找到的“心灵回音室”,它让我们可以独处,它让我们可以阅读,它让我们不再在坦白、出庭、牺牲中写作,不再为了注意力经济和公众关注度而虚构,它让作者之死的作者重新回到文本的时代,“因为我们拒绝主观性的消失,而与文学的频繁接触,则让主观化变得可能;因为我们还不打算放弃文学实践中具有建构性的主体间的相互性。至少,这是我所期望的。”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59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