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8-25【“百人千影”笔记】沃尔克·施隆多夫:父亲送我一面铁皮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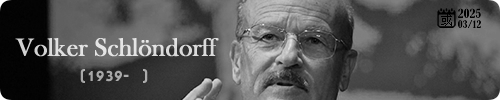
因为我可以只专注于画面,我很清楚讲故事不是自己最擅长的方面,因此我总是去改编文学作品。
——沃尔克·施隆多夫
他说他有“满抽屉自己写的剧本”,却在改编他人作品中成为“拍摄文学作品的教皇”;他不喜欢好莱坞的制片体制,喜欢独立制片,但是他认为独立制片是惩罚,也是艺术特权;他认为改编有难度的小说能刺激想象力和知识结构,却常常在“挑战自我”的过程中改变了固有的风格……当专注于电影画面的沃尔克·施隆多夫期望在别人讲述故事中发挥自己最擅长的一面,但是这肯定式的追求却在否定式的实践中成为了一个“施隆多夫的悖论”:渴望拥有一种庇护自身不足的存在,却在政治信念、道德理念、宗教信仰甚至爱情乌托邦中,演变成了放大自身不足的“铁皮鼓”——寻找父亲的隐喻,最后成为了无父的寓言,而施隆多夫似乎也成为了那个永远长不大的“奥斯卡”。
罗伯特·穆齐尔、海因里希·伯尔、君特·格拉斯、马塞尔·普鲁斯特、阿瑟·米勒、马克斯·弗里施、尤瑟纳尔、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在沃尔克·施隆多夫的电影生涯中,这些文学巨匠组成的长长名单,使得他一直汲取着他们文本的营养,而他们的文本构成了施隆多夫电影的“父本”,这是他寻找父亲的一种努力。从某种意义上说,将这些巨匠的文本变成电影,是他在文本世界里找到了和自己共鸣的东西:当他尝试拍摄第一部电影时,就发现了罗伯特·穆齐尔的《青年托乐思的迷失》里有着他想要的一切:“《青年托尔勒斯》里发生的情况和我在寄宿学校的经历很类似,托尔勒斯那种如同观察者般凌驾的态度使我产生了共鸣,我想既然穆齐尔都已经写好了,我可以拿来用,那为什么不呢?”
施隆多夫轻而易举就把罗伯特·穆齐尔放在了编剧名单里,但是对于施隆多夫来说,他不费多少力气就找到的“父本”,并不是一味照搬他的故事,他认为,这只是一种对话的开始,当对话发生,它其实已经消化成自己的一部分,而且,“原小说越难,拍成电影的效果就越好,困难的小说会刺激你的想象力和知识结构,使你呈现出最好的状态,这是一个自我挑战的过程。”这是一个从“父本”寻找自我的理想化阶段,但是这个“施隆多夫化”的过程在最后成为一部电影时,显然其中体现出来的价值观也都中规中矩、不偏不倚:在《青年托尔勒斯》里,没有了“母亲腰间升腾起来的掺杂着一点香水味的气味”,也没有特尔勒斯“要做一个女孩子”的内心欲望折射,那个受虐者巴西尼也不是拥有贞洁、苗条充满肉欲的瘦——施隆多夫去除了一切和肉欲有关的情节和描写,肉体不再是欲望的展现,它只在被折磨中成为痛苦的代名词——从生理性的折磨和受虐直接过渡到了精神性的痛苦和残忍,无疑施隆多夫走得是一条直线;截取了普鲁斯特小说《追忆逝水年华》其中一章改变的《斯万的爱情》,在施隆多夫手里,似乎在对于爱的追寻中实践着意识流风格,但这是很粗浅的一种认识,时间在意识流中也不是只是呈现于对一个夜晚的回忆,甚至自始至终根本看不出斯万的爱,而奥黛特对于斯万的爱更无从谈起,而要把这种所谓的爱称之为艺术,太过牵强;根据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小说改编的《使女的故事》中,施隆多夫没有更多着墨于基列共和国的外在秩序,而是围绕着凯特的命运转变,而在这个转变中,对于她女性维度的多重阐述显得机械,在缺失了开放性隐喻的剧情中,凯特甚至从来不具有对自我的体认,甚至作为最基本的妻子和母性女色在尼克的感情里逐渐淡化……
改编名著是一次冒险,自我挑战是一种痛苦,“拍摄文学作品的教皇”这一称誉的背后或者还有一种对施隆多夫缺失自我剧本的讽喻——除了根据阿瑟·米勒的《推销员之死》改编的同名电影较好地调动了电影元素,真正以自我挑战的方式将其变成了电影:施隆多夫对于这一个死亡事件的描述完全在自由状态中,他甚至用意识流的手法把“推销员之死”变成了一种现实版的梦境,在不同场景的交错和融合中,在人物随着剧情而自由出入中,影像镜头变成了流动的舞台,在间离效果的不断运用中,一种死变成了生的一部分,它在必然意义中成为了一个失败者无法逃避的选择。为什么施隆多夫在“父本”里难以逃离父权式的影响?为什么不能将满抽屉的剧本变成自己的剧本?施隆多夫为了弥补自己讲故事方面的不足而汲取了名著的语言张力,看起来是一种借鉴,但实际上,在用别人的文本说着别人的命运,自己仿佛就是一个旁观者,而这种旁观式的身份注解,也使得他难以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父亲。
作为战后成长起来的一代,施隆多夫需要在探寻中找到自己的王国,不管是不是乌托邦,他首先想要的是一个能让自己快速成长的庇护所——在童年时他经历了“二战”的最后时光,1944年一颗炸弹落到他家的阁楼上,门窗都被炸飞了,而在几个月前,母亲在二楼煮地板蜡,一颗火星引燃了整个厨房,液体的地板蜡变成了喷射的火舌,于是他在剩下的岁月里只能依靠照片来怀念母亲。炸掉的阁楼和失去的母亲,成为他缺少庇护的象征,所以他之后的人生几乎总是在寻找这样一个庇护所。在法国学习和生活15年,曾担任法国“诗人电影”导演路易·马勒、新浪潮电影大师梅维尔、阿伦·雷乃等的助理导演,这是施隆多夫走向电影世纪的一种经历,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以及那个被打开的电影世界,就是他寻找到的庇护所。这是一种现实意义中的庇护,当他从《青年托尔勒斯》开始,在巨匠的“父本”里找到了一种完全可以拿来拍摄电影的剧本,这是文本意义的庇护,而在电影世界里,施隆多夫开始信誓旦旦建造他的电影王国,其中的政治、宗教、道德和爱情,成为他寻求对个体和群体进行保护的存在,于是一种父式的主题成为他电影中的庇护所。
但是这种庇护是在破中而立的,施隆多夫首先是一个批判者,他要在批判中是想要清除历史的阴影,《青年特尔勒斯》揭露了军事学院的腐败和严酷,控诉了法西斯主义残酷迫害犹太人的罪行,是对早期法西斯精神的声讨;《肉体的代价》则通过事件的全过程展现女主人公的不幸遭遇,真实揭露了政府的残忍和刚愎自用、新闻媒体的无中生有诽谤造谣的内幕,电影一举打破了西德电影中的政治禁区;根据君特·格拉斯的同名小说改编的《铁皮鼓》,描绘了法西斯统治下的德国市民的精神空虚和生活真相的荒诞,以一个会把玻璃喊碎的孩子的视角来观察这个历史旋涡中的社会——《丽塔传奇》、《十分钟年华老去》、《第九天》以及《德国之秋》都涉及德国纳粹时代、当代德国社会极右派、极左派恐怖分子的题材,无不显示了施隆多夫直面现实的勇气。
但是,在这些批判性电影中,施隆多夫在揭露社会现实的同时,却并未找到真正合理性的制度和信念存在,无论是政治还是道德,无论是宗教还是爱情,似乎都在最后变得简单化,甚至流于扁平和庸俗:《玻璃玫瑰》里,施隆多夫试图用命运的巧合来解读一个爱上女儿的男人的种种遭遇,只是一种借口,最后自己存在而所谓的爱不存在,在唏嘘中没有自杀的勇气、用墨镜遮掩自己,也只是对于父性责任的拙劣掩盖;《使女的故事》中,基列共和国本身是荒诞的乌托邦,它在取消女性独立意义中构筑了“使女”这一神话般的存在,而凯特和尼克在施隆多夫“脱下红色”的命运大转变中,构筑了更为荒诞的乌托邦;施隆多夫78岁高龄拍摄的《重返蒙托克》,只是简单的一个“出轨”故事,其中的所谓后悔,所谓“人生错误”,也无非是冠冕堂皇的借口,施隆多夫最后的结论表达了他对人生哪个层次的领悟,这个糟糕的过程都让这种体悟变得廉价。
“我曾很长时间地相信乌托邦,现在则没有什么确定的政治信仰。一个人拍了一辈子政治性电影,现在由于没有确定的信念而停止拍摄这样的电影,我必须承认,这确实是一个道德领域的问题。”他把政治信念建立在社会道德判断之上,当施隆多夫在政治信念上找不到出路,甚至将其理解为一种“正义”式的与生俱来的概念,无疑所谓的道德判断也消失了;而宗教信仰呢?施隆多夫在《第九日》中试图寻找纯粹的信仰,但是牧师之所以活下来,真正的原因却是“幸免于难”——一个成为幸运者的牧师,对于上帝是不是开始存疑?“上帝为什么会允许纳粹和二战这样的事情发生?”施隆多夫对此的回答是:“真的存在上帝吗?我不知道答案。”正是因为现实中的政治、道德、宗教和爱情无法起到一种庇护意义,施隆多夫在电影中更是传达了一种没有答案的疑问,当他试图在普世意义上建立属于人类自身的庇护所,无疑在没有确定的政治信仰、道德判断消失、不知道上帝是否存在,以及对于爱情中的欲望如何拿捏的时候,施隆多夫反而陷落在所谓的乌托邦里,而那种对于父亲的寻找终于变成了“无父的寓言”。
《推销员之死》中威利作为推销员也是作为父亲,最后死于自我难以改变的命运;《玻璃玫瑰》在宿命论的借口中,让父女之爱变成了乱伦之爱;《乌尔詹》中“贩卖词语的商人”最后放弃寻找,在仪式化的父亲死去之后留了下来;《使女的故事》在政教合一的权力中,女人成为借腹生子的工具,完全取消了父亲存在的人性意义——施隆多夫所要寻找的父亲在哪里?也许在真正属于施隆多夫的两部电影里可以解读他的迷失,他的解构,他无父的寓言。《太阳神》是施隆多夫电影目录中容易忽视的一部,施隆多夫用“巴尔”这个名字命名主人公,他既是太阳神,也是恶魔,而这种神魔结合的产物,正代表着父性的矛盾性甚至对立性。“巴尔”从天上的子宫里降生,成为写诗的诗人,但是在大地之上,他带来的却是淫荡和邪恶,“爱情在天地接壤处。”当他写下这句诗,其实就是以父的名义建立了一个恶魔的世界:巴尔从爱欲的资产阶级酒馆和个人主义的阁楼走出,不是走向纯洁的自然世界,那些树木,那些原野,那些被人类废弃的车辆,都不是返归自然的表现,而是巴尔所建立的虚假的乌托邦,他以自然之名赶着罪恶的勾当,当然,他已经写不出一句诗歌,他已经看不见天空,他已经忘记了自己的过去,“过去是个奇怪的词”,他这样说,于是在苏菲的哀求中,在埃德加的冷漠中,在泰迪的死亡中,他只是喝酒,只是吃东西,只是想要更多的钱,甚至他让苏菲把肚子里没有出生的孩子埋在泥土里,看成是对自我的一种赎罪——大地挤满了罪犯,不是因为大地本身的罪恶,而是有着像巴尔一样的罪人。
从天空到大地,从出生到死亡,巴尔完整地描绘除了一条轨迹,但是在天地接壤处的爱情,除了欲望一无所有,所以当爱欲让女人怀孕,那个未出生的孩子注定没有父亲,不管是所谓的爱,所谓的孩子,所谓的自然,其实都是一种欲望,而且是邪恶的欲望,是肮脏的欲望,是名为自由实为自恋的欲望,是自我膜拜的欲望,而最后的死便是这欲望剥落了所有伪装而成为罪恶的象征。与其说孩子被埋于土地而没有父亲,不如说太阳神巴尔本身就是一个父亲,但是这样的父亲永远不是为了给出一个命名了爱的庇护所,它和欲望在一起,和死亡同行,最后的巴尔甚至也成为了一个得不到庇护、无父的孩子,“我吞噬了死亡却一无所知”——父亲制造了邪恶,父亲也在逃避现实。
另一部渗透着父亲寓言的则是《铁皮鼓》。一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像是永远不想要父亲的存在,在这里父亲是缺失的,是主动拒绝后的缺失,也正是在这种缺失里,奥斯卡才会抛弃承认世界的规则,从而让自己成为父亲,但是这一过程里充满了暴力和情欲:在父亲强奸玛利亚之前,他已经变成了一个父亲,他把小库尔特当成了自己的孩子,他对他说,在你三岁生日的时候,我会送你一面鼓,他抱着他的时候说:“库尔特,你是我的儿子。”这是一种自我命名的父子关系,而实际上,三岁,一面鼓,乱伦的关系,就像是奥斯卡对于自我的一次命名;但是当父亲和母亲去世之后,这种自我命名又以扔掉那面铁皮鼓的方式让自己成为真正的父亲,随着小库尔特那块石头击中他,在他血流而倒下的那一刻,他开始长高,开始蜕变,开始成为真正的父;最后在被攻克柏林的苏联军人枪杀的时候,奥斯卡喊出了一声“爸爸”,混乱、阴暗、充满着恐惧和哭声的家,终于以父亲的死亡画上了句号,面对身体被子弹洞穿的父亲,面对全身流淌着鲜血的父亲,面对和纳粹德国一样死去的父亲,奥斯卡的那一声“爸爸”似乎是看见暴力的害怕,似乎是看见死亡的恐惧,但更多的是,因为自己如同游戏一样的惩罚让父亲失去了活下来的希望,自责、忏悔和无法救赎的罪恶之外,不管是让他迷失的父亲,还是自我命名的父亲,都在最后扔掉铁皮鼓中成为一种告别——告别父亲。
从别人书写的“父本”,到电影里对父亲的寻找和迷失,再到父亲隐喻式的建构和解构,施隆多夫在多义世界里搭建那个庇护所,但是乌托邦消失了,理想主义不见了,现实中的政治信念、道德规则、宗教信仰也都无法成为一种力量,施隆多夫更像是一个在电影世界的推销员,他售卖着别人的商品,永远以父亲的名义自居,想象着未来的儿子成就伟大,而其实一种预感早就化成了光和影,在无父的世界里迷失:“这个剧本让我感动得流下泪来。难道我不就是威利·洛曼吗?我前往世界各地,为了推销自己的商品,却很少能卖出去什么,但是却能给自己描绘出一幅美好的幻象?我眼前浮现出一条长长的黑暗的走廊,贴着蜡墙纸,一个小个子男人出现在走廊尽头,一个剪影,拖着两个装满了剧本的箱子,预感到没有什么好结果……”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52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