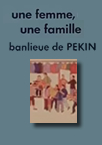2023-06-15《一位妇女,一个家庭》:个体作为革命者

“一位妇女,一个家庭”,并列的两天线索,都是单数的一种呈现,这是伊文思团队拍摄《愚公移山》中较少以个体为拍摄对象的纪录片:《渔村》反映的是渔民群体的生活,《上海电机厂》则是对工人阶级的展现,《球的故事》是学校教育的整体叙事,《一座军营》则是对军队生活的记录,《大庆油田》是一曲发扬“铁人精神”的建设者的赞歌,《对上海的印象》是对上海这座城市的介绍,《北京杂技团练功》《手工工艺人》和《北京京剧团<龙江颂>排练》则侧重表现了文艺工作者的群像——只有12分钟的《秦教授》是关于钱伟长这一个体在文革中受到思想改造的记录。
和《秦教授》只有12分钟的“短制”相比,《一位妇女,一个家庭》则是一部101分钟的纪录片,在《愚公移山》中也属于长片,所以伊文思并不像《秦教授》那样,只是展现一个侧面,一个局部,而是以单数的个体反映一个群体,反映一个时代,这就决定了在这部剧集里,伊文思团队要采用一种以小见大的叙事方式,以点到面表现从个体生活到社会生活的重要方面:“一位妇女”是“一位家庭”中的妇女,“一个家庭”是一个社会中的家庭,是一个时代中的家庭,所以,“一位妇女”也是社会中的妇女,时代中的妇女。“一位妇女”是高淑兰,那么伊文思团队在拍摄时选择她,“一位妇女”身上到底有怎样的特殊性和代表性?
从资料上看,高淑兰绝不是一个普通妇女,这个贫农出生的妇女,文化大革命之前就在北京的“二月七”工厂工作,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成为工厂的骨干,之后成为该厂解体车间主任兼党支部副书记,196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成为工厂的工会副主任,1973年在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伊文思在纪录片中并没有提到高淑兰中央后补委员的身份,说及的是工会副主任这一领导职务,或者纪录片拍摄早于中共十大,或者伊文思团队故意不说到高淑兰的这一身份,使她仅仅在“一个家庭”和一个工厂里展现个体的生活和工作。
所以在“一个家庭”里,高淑兰的身份就是一个妻子,一个母亲,住在哥哥家里,她则是妹妹,是老妇人的女儿,这样的身份倒是普通的,所以在前半部分展示高淑兰家庭生活的故事中,伊文思的镜头里展现的是家庭生活的浓浓烟火气:早上她在菜市场里卖肉买菜,回到哥哥家里之后,给了女儿小红糖吃,小红在摄影机前面跳舞还唱起了“红太阳”;一家人浇花,包饺子,说起邻里关系,其乐融融。但是,伊文思拍摄高淑兰相关的家庭生活,并非仅仅是对一个普通女人的展示,他以高淑兰这一个体连接起了社会和时代,其中叙事的方式则是对比法:母亲说起自己生了9个孩子,有4个死了,说起自己8岁就成了童养媳,结婚就是“用一个闺女换一头猪”,还说起旧社会对女人的要求就是有小脚,那样才能嫁人;高淑兰的哥哥也说起自己是贫农出生,自己19岁结婚,是包办婚姻——高淑兰插了一句:“他们是先结婚后恋爱……”母亲和哥哥都曾经生活在旧社会,旧社会所受的苦自然成了他们闲聊时的回忆,而所有这一切的回忆就是为了突出新社会成了主人,“现在一切都结束了。”以前旧社会要交税,现在哥哥嫂子一个月工资110元,房租费用只要7元钱;以前只有在过年的时候吃一顿饺子,现在则是家常饭……
| 导演: 尤里斯·伊文思 / 玛索琳娜·罗尔丹·伊文思 |
高淑兰虽然生在旧社会,但是她却长在新社会,她说起和丈夫结婚,不再和哥哥嫂子一样是包办婚姻,更不像母亲那样是童养媳,她在25岁结婚,结婚之前两个人只吃了一顿饭,“不能让对方请”,这就是所谓的平等;高淑兰说起结婚之后夫妻基本上没有吵架,关系很融洽,这就是双方的尊重;而当问起是不是还要小孩,一边的婆婆似乎想要他们生一个,但是高淑兰说自己不要了,想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和学习,这就是所谓的自由。这种平等、尊重和自由,所折射的正是妇女的地位,它从“一个妇女”的故事变成了新时代、新社会所有中国妇女的现实。
而妇女地位的变化更突出地表现在高淑兰在工厂中的生活,她以前是一名普通女工,但是现在成为了工厂的工会副主任,这也意味着她成为了工厂的领导,在这个大厂里成为领导意味着什么?“二月七”厂历史悠久,1923年2月7日在中国铁路工人大罢工中,这家工厂就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大罢工,在罢工中有6人牺牲300余人受伤,也许是为了纪念这次大罢工,工厂便有了现在的名字,这是一个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工厂,这个工厂到底是怎样一个规模?伊文思没有说到工厂的工人总数,但是有两个细节表明了这家工厂的规模:在哥哥所在的四合院里,打牌的那些人几乎都是这个工厂的工人,一个四合院有7个家庭38个人,伊文思用俯视的视角拍摄了这一带的四合院,可见这片居住着很多工厂工人;说到孩子的教育,这里除了托儿所还有小学和初中,“这里有5000个孩子”,5000个孩子可见工人的数量之庞大。
在这样一个有着革命传统、工人数量庞大的大厂里,高淑兰能成为工会副主任,的确有她的过人之处,在伊文思的镜头前,很多她的同事对高淑兰做出了评价:有人回忆说她当时进场的时候只有16岁,一个初出茅庐的小女孩有点羞涩;还有人说高淑兰有魄力,很勇敢,像个男孩子,很多男人不敢做的事她都会去尝试;有人则说到了她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站在第一线,和阶级敌人作斗争,积极捍卫毛主席提出的“16条”……高淑兰果敢的性格,也是女性地位不断提升的写照,厂里的女工人就说起自己的车间,女性已经占了四分之一,以前“头发长见识短”的旧观念已经不存在了,“男人能做的事我们也能做……”当然高淑兰就是这方面的典型,她在伊文思提出为什么能走上工会副主任这一领导岗位的回答是:因为我们要为工人服务,她说工会有三大内容的工作,一是政治教育,二是技术培训,三是提高工人的生活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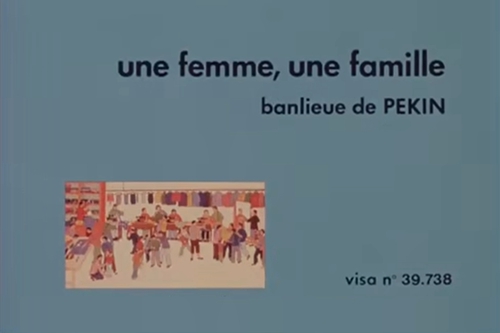
《一位妇女,一个家庭》电影片头
三项工作,对于高淑兰来说,似乎第一项工作永远摆在首位,而这也是她在文革中成为工厂骨干和革命者的原因,身为工会副主任,她现在还在思考如何加强工人的思想教育,而要让工人提高思想觉悟,自己当然不能退步,她之所以不想要更多的孩子,就是因为要把时间花费在工作和学习中,高淑兰甚至说了一句:“家庭生活不是全部。”这就是伊文思“个体作为革命者”的具体体现,但是在从家庭到工厂对高淑兰做全面展示的时候,在镜头后面的伊文思其实也带着一种思考:当一位妇女在革命中表现胆识和勇气,当妇女走上革命领导岗位,有所得是不是也有所失?同事们说她果敢,但也有人说她工作方法有些简单,有些做法不够严谨偏于主观,甚至暗示她容易骄傲自满,希望和群众打成一片。
伊文思只是借高淑兰同事的口说出了一些意见建议,而他直面高淑兰的一个问题是:我们在拍关于你的电影,容易引起一些看法,你怎么看?高淑兰只是笑笑,她并没有过多考虑聚焦自己一个人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后来她说作为领导要多为工人着想。于是在很长的篇幅里,伊文思的镜头没有直接对准高淑兰,而是拍摄了工厂建立“三加一”小组、实施技术创新项目、废物回收利用等镜头,这种风格和《上海电机厂》的叙事风格相似,似乎也是伊文思对个体太多渲染的一种回避。实际上,在这部剧集中,伊文思对“一位妇女”的展示还是显得片面,一半的内容是在工厂里拍摄的,而另一半涉及“家庭”的故事,也并非是真正从高淑兰这样一个个体的视角来叙述的,她是作为四合院的一部分,作为哥哥家的一份子,而自己的家庭生活几乎没有涉及。
高淑兰每周一次坐火车回到北京自己的家,其他时间住在离工厂更近的哥哥家,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一方面是为了工作,另一方面丈夫是一名军人,所以在仅有的一幕夫妻相见中,穿着军装的丈夫来火车站接她和女儿,然后三口之家回家,仅此而已,按照高淑兰自己的说法,和自己的性格不同,丈夫平时比较内向,所以伊文思只是简略地拍下了两个人的见面和三口之间回家的镜头,而没有对家庭生活进行更全面、更细节化的展现。没有自己的家庭生活,甚至丈夫也只是露出了一个侧面,在某种意义上,属于高淑兰的“一个家庭”成了某种缺席,而这是不是也在表达着“一位妇女”成为革命者,在另一种层面上身份的缺失?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33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