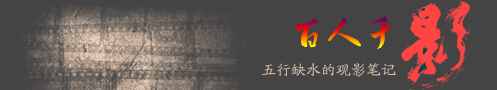2020-12-31六弦琴

购买了12升的瓶装水,取出最后一份都市快报,结束“运动健康”里的968次步行……一系列动作在最后一天发生,是准备迎向翻过日历的“跨年夜”。但其实,最后一天的终结意义不是为了让目光向前,而是在抬头望见黑夜低头注视大地中,回望即将走完的2020年,明月照耀下一个人的影子是被时间拖长的影子,总在灯光和身体的后面成为走过的这闰年366天一种注解。
翻到第一页,那时时间被开启,“应该,回到现场”成为起点时的一种行动,“不是回到现场,而是当你真正在当下的时候保留现场、记录现场,所以每一天都应该进入现场,每一天都应该被标记,每一天也都是不可复制和不可追忆的现在。”进入现场,记录现场,标记现场,是不可复制的现实,上面被标注的是“非典型”事件:从“疫”起过春节开始,所有的秩序和规则都被改变了,生活被 “卡”在二分之一的冬天里,不断叙述着“冬日残酷物语”,无法逃离的境遇,是传说变成现实的疫情,是提升至红色的预警,是被封锁的道路,人人都是一座孤岛,没有进口也没有出口,只有在密闭的口罩里的呼吸,声音传达不到对面,世间都是病态。
渺小如整体的存在,一切在混乱之后开始丛生:沉默丛生,困顿丛生,嘈杂丛生,深渊丛生。在丛生而被湮没的世界里,一具身体如何在丛生中变成独立的存在?“放松,就是现在:扣下去。”不是等待现在的到来,在进入封闭时间的漫长过程中,所有的日子都不是等待的结果,它甚至变成了一种虚无,在无法触及真实存在的境遇下,九月末日终于破裂开花:那开窗的七楼是可以俯视的,那同样开窗的三楼是可以平视的,垂直的平移其实不需要身体做任何抵达的动作,在自动式的下降中,一切都没有悬念,工作之一种,生活之一种,“扣下去”的习惯性动作,五十码只是一个开门和关门的瞬间。是的,一切都在双脚的瘸行中被改变,从夏天到秋天,时间是一瞬间,从七楼到三楼,空间是一瞬间,一瞬间构成的时间在反复,在重复,但已经没有可能的创造力,于是,滑行一般,落于平台一角,一种“搁置”的状态,甚至连起立也被取消了。
所谓搬离,是更大的调整,十六年的位置再无人坐下,而新造的屋子里,都装满了行走的人,所谓改革无非是一种试错,在混乱却空荡的角落里,人物已经退场,故事已经湮灭,时间已经作古,昨日之后的今天,离开之后的到达,告别之后的开始,都像是从没有灵魂开始的某段旅程,看见或不看见什么,遇到或不遇到谁,都变成了远方的一次或然。但应该留下点什么,应该叙说点什么,甚至只是应该记录下什么,春末夏初的日子却必须告诉一个秋天的消息,那只不过是从2008年秋天开始的一次命名,当自己走在自己的时间里,呼吸着自己的呼吸,看见着自己的看见,言说着自己的言说。于是,“或。历”被开启:2024年9月27日,星期五,是虚拟却真实的秋天,天气未明,人物未明,事件未明,即使一切都是一无所知,在“同一个,另一个”的秋天,只有自己是明白无误的:我闯入了时间的另一个通道。
唯一的通道,唯一的自己,唯一的记录,以及唯一的时间,当单数聚合成“或。历”的复数,它必定会超越一种惯常的时间叙事:从2024年9月27日到今天的2025年9月2日,“或。历”几乎已经走过了整整一年,立春时留下了“念去去十万八千里”的印记,春季开始时看见了暗夜里“六千张面孔的鱼”,盛夏时节开始“往身上洒了点水”……惯常只走过了不到六个月时间,“或。者”却早已经跨年,早已经周岁,早已经用自己的目光探寻无人经过的那条路。在远离了2020年日常叙事的命名中,我书写,我阅读,我观影,我行走,世界是封闭的,只有自己的目光触及了虚无和实在,世界又是开放的,它随时可能改变秩序和态度,随时会把自己叫做时间的制定者:547篇博客里,有着12年如一日的坚守,160册阅读的图书中,有着一个不被打扰的他世界,284部电影里有着“百人千影”的经典光芒和“年度电影”的时代印记……
数字总是被直观地呈现出来,它是复数中的一个整体,但是当这个整体是从一次次经历中叠加,当这个整体可以分离出焦虑和收获,整体并不是简单的总体:547篇博客中还有着被时间拖向未知而留下的“未完成”状态,7篇影评和15篇书评,成为一个断裂的缺口,在无法被改变的24小时内,它们都在存目而游离中让整体不再坚实;160册图书的阅读创下了历年之最,但是82万字的书评里有多少已经逃逸了思想,甚至购入的103册图书,是2016年之后第一次突破百册,但是在未阅读和已阅读最后成为物的状态中,又有多少会变成一种拥塞?“百人千影”和年度电影,是在一种既定的轨道中滑行,当自我的时间和惯常的时间发生冲突,那被延宕的感觉又在何处放置一个清晰的结尾?
数字生活中的种种疑问,其实都是无解,它只是被陈列在从第一天到最后一天的物理空间里,而当走过了更错综更庞大更无助的366天,空间世界里留下了一点点突围的印记,影像中的“纪录片”是为了看见世界,是为了记录生活,从10月的西湖国际纪录片大会,到12月的广州国际纪录片节,不是闯入其中成为观者,而是本身就在被记录的过程中,有我和无我,连接在一起,在现场,在当下,“一切的纪录都是有意义的。”就像一部私有的纪录片,意义就是过程本身。于是在影像之外,在记录之外,行走也成为一种没有过去没有未来的现在时,从良渚到“两山理论”的安吉余村,再到南堡,在宏大历史和政治之外,发现的是一个被定格在现在的场域,而更远行的贵州施秉和广州,也都在一种离心的渴望中,变成“或。历”中独一无二的存在:从高原到平原,自西而东,梯级过渡,演绎了从经过到离开的过程,也许只有匆匆定格的瞬间,才是一个被看见了真实,又在现实中书写成文的施秉;穿过了南方以南的城市,穿过了熙攘的人群,穿过了陌生的街道,然后走进天河广场,走进百丽宫影院,坐在一个人的位置上,进入确定性的当下……
第一天“应该回到现场”,最后一天在数字中回望366个现在,合上的一本书,结束的一次行走,完成的一次命名,在这个人为定义的2020年变成最后的象征物,而一个人带着必然的影子逃离出来,在没有象征的世界里,明日如昔。
阅读:
观影:
行走:
·五千年的一道裂隙
·误入藕花深处
·云台山:“后身体时代”的行走
·施秉风情
·抬头也看天
·南方以南的当下
·黄埔军校旧址:革命尚未成功
·广州风情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25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