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09-19 【“百人千影”笔记】玛格丽特·杜拉斯:她说,以及无限阅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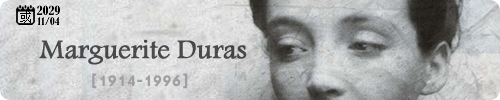
“当我在拍电影时……我和电影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将其谋杀掉的关系。”
——玛格丽特·杜拉斯
在关于电影和写作的书里,她说:“影像是不能被诉说、被描述的,它就只能是那样,是不会变的。”在面对伯努瓦·雅克的镜头时,她说:“被阅读的书是向别人开放的……”在1972年导演的电影《Jaune, le Soleil》中,她说:“黄色,太阳,一团熄灭的火……让世界毁灭吧!”她在说,她又说,她还说,所有的她说都指向了电影,指向了电影的阅读,指向了电影的叙事,作为居伊·德波“景观社会”坚定支持者和实践者的玛格丽特·杜拉斯,以不断重复的“她说”方式喊出了居伊·德波的宣言:“电影必须被销毁!”但是,玛格丽特·杜拉斯也拿起了摄影机,也完成了十七部电影,也成为了实验电影的导演,当“她说”建立了“谋杀”的关系,是用她写作的笔谋杀了拍摄的摄影机?还是用摄影机谋杀了自己创造的影像?
玛格丽特·杜拉斯,对这个名字的认识很多是从作家这个身份出发的,之后是电影编剧,然后是电影导演,从纯粹文字书写到为电影编剧再到拍摄电影,玛格丽特·杜拉斯所走的是一条从文字到影像的转变之路:1943年,从法属印度支那出生地来到巴黎定居仅仅一年的玛格丽特·杜拉斯,将自己的姓改成了父亲故乡一条小河的名字,也是在这一年,她用这个名字为笔名发表了《无耻之徒》,文学就是玛格丽特·杜拉斯自我命名的一种仪式;1958年出版小说《麾狄拉特干达毕业》,玛格丽特·杜拉斯因此被誉为新小说代表作家之一,一年之后导演阿伦·雷乃邀请她为《广岛之恋》撰写电影剧本,这部电影在法国引起巨大反响,创下了很高的票房纪录,她的名字也家喻户晓;1967年,玛格丽特·杜拉斯正式拍摄电影,她推出了自己第一部剧情长片《音乐》 ,从此开始了自己的电影创作生涯。
从文学转向电影,对于玛格丽特·杜拉斯来说,并非是非此即彼的一元化选择,她的创作可以看成是“一手握着笔一手拿着摄影机”的混杂状态,而在这种混杂状态中,左手真的能消灭右手吗?或者说,玛格丽特·杜拉斯为什么要赤裸裸而暴力提出“将其谋杀”?或者可以认为是她对自己的一次证明,《广岛之恋》取得成功,《情人》造成泛滥,这些电影都和她的小说有关,选择拍摄电影是因为她无法忍受别人将她的小说“加工”成了电影,她就是需要证明自己的小说也可以变成自己的电影;或者是对自己创作小说的一次阅读边界的拓展,她于1975年拍摄的电影《印度之歌》就是根据自己1965年的小说《副领事》改编,是这部至今公认为杰作的电影让观众和读者重新去阅读小说;或者是因为玛格丽特·杜拉斯拒绝商业和娱乐化的电影,她要用最纯粹的电影守卫电影的“理想国”……
种种的或者,其实都是将电影看成了玛格丽特·杜拉斯的一种证明工具,在这种工具的“使用”中,玛格丽特·杜拉斯显然不会有一种“将其谋杀”的欲望和行动,谋杀是为了破坏而毁灭,是为了颠覆而否定,不是为了新生而是为了死亡。这种“我和电影”关系用形象的话来说,就是用电影击败电影,用电影解构电影,用电影消灭电影——前一个电影是“玛格丽特·杜拉斯的电影”,后一个电影是传统意义上、用画面运动、对白等电影叙事完成的电影。在电影击败、解构和消解电影的谋杀行动中,玛格丽特·杜拉斯显然是在进行“一个人的战争”,一方面他认为传统的电影封闭和限制了想象,当巨大的投资折断了想象的翅膀,电影意味着愚笨和乏味,所以在人们疏远电影的时候,电影就走向了死亡,这是一种电影传播学甚至电影社会学层面的解读;另一方面,玛格丽特·杜拉斯认为电影限制了剧本,剧本限制了文字,所以电影也扼杀了文字具有的想象,在她看来,“文字具有一种无限繁衍的能力……被拍出来的影像是有形有象的,但文字却是无形无象的。”一言以蔽之,文字在影像中死去,而“一个字却能包含数以千计的影像”。
一方面和另一方面,其实是合一的,玛格丽特的文字里常常是表面看起来是空洞、扁平、模糊的形象,但是他们的内心充满渴望和激情,在一种不确定、不完整以及零碎、断裂中造成了悬置、紧张,那些句子是是音乐,在独特的氛围里文字仿佛自己在讲述。所以当玛格丽特·杜拉斯拍摄电影,她不是将电影看作是文字表达新的载体,而是完成“谋杀电影”的任务并将其推向死亡——这或者就是极度自恋的玛格丽特·杜拉斯对于文学创作的另一种极致表达。而谋杀电影在玛格丽特·杜拉斯那里表现为一种暴力式的毁灭,那就是以彻底的“声画分离”方式构思出一套“无依无靠”的电影摄制技术,将电影变成一种声音和画面自行运转的系统,让声音自说自话,让画面自由流动,各自朝着自己的方向完成“写作”,“我把电影视作写作的支撑。无须填写空白,我们在画面上挥毫。我们说话,并且把文字安放在画面之上”。”
1967年的《音乐》是玛格丽特·杜拉斯电影实践的试水,但是很明显,这部电影是玛格丽特·杜拉斯电影中最传统的一部,但是在这个传统的表象中,玛格丽特·杜拉斯通过三个人围绕一起离婚事件表达了“死亡”,他们在回忆中滑行,但是最后却始终无法抵达最终的目的地,于是回忆之旅在“一切都结束了”中结束,“也包括死亡?”电影中的这一疑问更像是玛格丽特·杜拉斯对传统电影叙事态度——两年之后,玛格丽特·杜拉斯终于在“毁灭”中开始了“她说”。根据自己的短篇小说改编的《毁灭,她说》是玛格丽特·杜拉斯第一次说话,而说话指向的是“毁灭”这个主体。毁灭,逗号,她说:“毁灭”来自于她说的话,第三人称,单数,毁灭是一个人的毁灭,是一个人被毁灭;而且来自于一个女人的述说,毁灭以及被毁灭和一个女人有关;毁灭,但是没有终结,逗号保留了继续的可能,转折的可能,以及否定的可能,当然,也有继续毁灭的可能;“毁灭,她说”,她在说,但是仅仅是说?不涉及行动的说?被推向深渊而无奈的说?那么在第三人称单数的她之外,在毁灭之外,在说之外,玛格丽特·杜拉斯是不是还有另一个世界?
她说开启了另一个世界,毁灭开启了另一个世界,这部电影是玛格丽特·杜拉斯旗帜鲜明“反电影”的一次实践,一方面是“她说”,她说是问题,她说是回答,但是所有的问题都没有走向所期待的答案,所有的回答也都变成了未知;另一方面是“毁灭”,只有声音,只有对话,只有问题和回答本身,它们都在能指的层面上滑动,从来不抵达所指;声音在画面之外,声音却在画面的内部,画外音其实已经进入到了画内场景中,即使是一种声画分离,叙事也可以将两者结合起来,只是它们之间不再是一种对应,就像问和答,总是游离在真实和虚构、探寻和未知之间;接着人物出场了,看得见的人物,画面中的人物,说话的人物,行走的人物,当然他们也是确定的人物,但是一切都不展现意义。
“毁灭,她说”,她在说着毁灭,毁灭却已经变成了行动,她害怕毁灭,她却早已经在客体化中变成了被毁灭的对象——于是这个毁灭的寓言在影像化的分离、异化中又回归到玛格丽特·杜拉斯的笔下,变成另一种文学叙事。这种“她说”带来的毁灭感,在1974年的电影《恒河女》中表现得更为极端。在电影一开始,玛格丽特·杜拉斯就在“她说”中将电影拆解,“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两部电影,平行于电影影像的是被播放出来的纯声音电影。为了避免任何轻视,我们想让观众知道,这两个声音来自女性,完全不属于在影像中出现的角色。可以补充说,影像中的人物完全不知道这两个女性的存在。”玛格丽特·杜拉斯将这种叙事称为“声画分离”:声音是声音,影像是影像,声音在叙述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成为了声音的电影;影像在讲述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成为了影像的电影——两部电影是完全独立的,是平行发生的,所以声音里的“谁”是对那个问题的回答,它指向的是“他们”,但“他们”也是一个“谁”,而影像里的“他”和“他们”也并非是在看见和被看见的层面上组成一个完整的叙事链条。
同样用声画分离造成两部“平行电影”也在《印度之歌》中得到了革命性阐述。这是一个“爱情故事”,这是对记忆的重塑,但是玛格丽特·杜拉斯说:“一切都建立在演员与人物的分裂以及声音和画面的距离上,造成了一种存在的微颤,一种妙不可言的不适,一种爱情燃烧的忧思”。全片74个镜头组成的是画面,500多个句子则是声音,它们共同组成了记忆,但是记忆不再是场景的如实复制,不是通过画面来传达,“人生从来都不是一部条理清晰逻辑紧凑的编年史,当人们经历这些事情的时候是不自知的,只是在后来,凭借着记忆,悟出了这些事物的发生”……所以在这种破碎的记忆中,一切都变成了主观感受,“我爱你,直到什么也看不见,直到什么也听不见。”记忆不在场,爱情不在场,印度、加尔各答、戴尔塔岛也都是不在场的,这里是沉闷,是潮湿,是压抑,是湿漉漉,是半梦半醒,更是疯癫,是疏离,是迷失,在一个找不到自己、找不到爱情、找不到自由的他者之地上,一切都是不在场的。
更重要的是,声画之间的关系也是不在场的,玛格丽特将声音系统和画面系统各自独立开来,声音在讲述,声音在对话,声音在议论,但是谁在说、说时的状态和表情如何,从来没有在画面中得到体现,而画面中的人物在行走,在跳舞,在镜子里,在对望中,都不发出一点声音,他们是沉默的,他们是无语的。说和不说完全分离开来,声音在画面中缺席,画面也在声音中缺席。这样的缺席造成的不在场恰恰是玛格丽特·杜拉斯建立的一种结构主义:当声音为主体时,画面就是声音的补充,就是声音表现的对象,而当画面为主体时,声音就变成了画面的补充,就成为了画面表现的对象,或者说,画面外的声音会指向一个画面系统,画面系统就是一个封闭的存在,同样,当画面需要声音来补充的时候,画面也不再是一个自足的系统,封闭却不知足。
很明显,玛格丽特·杜拉斯的声画分离是对传统电影叙事的解构,解构的目的是回到文字,回到句子,回到文学叙事,回到诗和散文,也就是说,在玛格丽特·杜拉斯看来,电影只不过是文学的一种形态,电影的拍摄和观看都是一种文本的阅读,在这种阅读中,情节、人物和事件,这些呈现在画面中的元素被玛格丽特·杜拉斯无情抽离了,电影变成了对剧情、场景和布景的反抗和取消。但是,当抛弃了电影声画结合这个自足的系统,电影叙事真的需要毁灭吗?阅读如何成为可能?《恒河女》的声音来自小说《劳儿之劫》,影像则来自《爱》,这些都是玛格丽特·杜拉斯创作的文本,如果在没有阅读这些文本之前观看这部电影,作为一个普通读者如何知道背后这两个彼此独立的文本?当一部电影将两个文本放置在一起,观众自觉地进行编码,在自我编码的阅读中,电影是不是会达到声画分离这种独特书写的叙事效果?会不会让观众得到平行电影带来的观影体验?
声音是一部电影,影像是另一部电影,声音和影像之间很难建立统一的叙事,声音不是和影像在相同的层上展开故事,声音也不是影像的补充,而影像也独自拥有自己的声音——可能的同一性是声音和影像同样弥漫着某种逝去的哀愁、陌异的悲伤,同样在表达着回来的空寂和死亡的压抑。但仅此而已,玛格丽特·杜拉斯从来没有打算要将平行电影变成一种单一性的存在,观众的编码是徒劳的,因为它在作者的解码中早已化为乌有,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观者的电影和作者的电影也变成了两部平行电影,无论玛格丽特·杜拉斯的实验具有怎样的开放性,对于观众来说,也仅仅是形式意义上的勇气。玛格丽特·杜拉斯乐此不疲,孤独而绝情地行走在自己的王国里,在《印度之歌》一年之后,玛格丽特·杜拉斯完成了将这种乌托邦推向极致的电影《她在威尼斯时的名字在荒凉的加尔各答》。
1975年的《印度之歌》,1976年的《她在威尼斯时的名字在荒凉的加尔各答》,隔着一年的两部电影并非是真正独立的两部电影,因为它们的声音系统是完全一致的,当画面变成全新存在,玛格丽特·杜拉斯对电影的完成或者只是在“拍”这个动作里。拍完画面,重新把一年前《印度之歌》的声音部分放置在了电影里,“另一部”便是对“原型”的改编,所以原型就是《印度之歌》,《她在威尼斯时的名字在荒凉的加尔各答》便成为了原型的一种延续,甚至是一种附属。声音不变,意味着讲述的方式不变,意味着故事不变,意味着声音叙事不变,但是它仅仅在声音系统里,杜拉斯给与声音一种“看见”的功能,更是把声音系统构建为自足的系统,不管画面如何改变,声音系统才是电影的主体,电影的核心。但是,当画面被替换,用另一种画面和声音系统组成一部电影,电影也意味着不再是唯一的文本,它是一种可组合的存在,它具有的是随意性,是这一部也是另一部:如果声音系统始终在恒定、自足之中,而画面换成了《毁灭,她说》,那么是不是这是一部名为《她在威尼斯时的名字在荒凉的加尔各答,她说》的新电影?如果换成《恒河女》的画面,是不是又成为《恒河女在威尼斯时的名字在荒凉的加尔各答》的新电影?再进一步,用其他电影的声音系统建立自足而恒久的系统,再配以不同电影的画面,如此,则可以生产出无穷多的电影。
无穷多的电影,是一种繁多的存在,一个自足且恒定的声音系统,是一元的存在,繁多和一元之间的矛盾,在杜拉斯那里都变成了实验的一部分,当电影不再具有唯一性,当声画变成随机的存在,听见而看见的电影还具有怎样的意义?杜拉斯当然是反传统叙事的,她以阅读电影的方式解构了观看电影的习惯,的确在叙事学意义上打开了一条可能的通道,但是这种把电影无限推向可能性文本的实验,在某种程度上动摇了电影本体论,实际上,这一切都是杜拉斯在不断阐述其作者意图,她完全忘记了电影作为文本还可以有读者意图和文本意图。一部电影,可以是完全主观的电影,可以完全是作者创作的电影,但是不可能将观者置于完全被忽视的位置——如果按照杜拉斯的这种电影本体论,观众可以毫不夸张地关掉声音,这是一个完全取决于他自己的行动,在只剩下画面的观看中,杜拉斯精心设计的声音叙事完全变成了一种无:还能看见什么?这还是一部电影吗?这是对读者意图忽视的结果,同样,忽视了固有的文本意图,声音系统再怎么讲述一个无限可能的故事,当画面不再是文本的一部分,我们为什么还需要影像?闭上眼睛听一本书即可。
关闭了读者意图,消灭了文本意图,杜拉斯无疑就是让一切都回到蛮横、霸权的作者意图中,以作者为唯一的核心延伸出一个故事,一种叙事,而且她就是把作者意图当成了一种精神的在场,其他的画面、影像和故事都只是“形象”,形象是缺席的,是虚构的,是可以充值的,是被用来替换的,只有形象背后的精神不变,只有读者背后的作者永在:即使孤独且孤立,杜拉斯仍然享受着至高无上独一无二的“作者”恩宠,而这是杜拉斯“反杜拉斯”的一次实践,因为“杜拉斯”也是可以替换、可以组合、可以更换的。玛格丽特·杜拉斯在这部电影里表现了最极端的解构,但这不是对电影的谋杀,而是在“杜拉斯反杜拉斯”的悖论中完成了一次孤绝的自杀。
从谋杀到自杀,玛格丽特·杜拉斯毁灭电影的意图达到了,但也将自己推向了永远孤独甚至孤立的状态,而这种状态源于她对写作的执念,在纪录片《写作》中,杜拉斯面对镜头表现出一种侵入式的不安,就像她的写作,“整座房子都在写作,跟我一样,一切的一切,到处都是文字。”房子在写作,地下室的苍蝇在写作,夜晚在写作,一切都在写作,写作就是写作本身,而她认为电影和戏剧是为了别人而打开的,在这种打开中,“它们并不自由,它们被制作,被规范。”所以把自己关闭在写作的孤独中,只有在被写作包围的世界里,杜拉斯才感觉自己是安全的,“在这房子里我们从来不扔花,这是传统,就算是枯死了也留在那。”像苍蝇一样,花也对自己开放,在疯狂而死去的状态下独自写作。但是正是这种对安全的极致追求,她反而是不安全的,因为身边的每一个地方都可能被打开,可能被看见,甚至被“谋杀”。
也许杜拉斯感受到了孤绝状态本身存在着危险性,所以从“杜拉斯反杜拉斯”之后,她有限地回归到电影叙事之中,发现电影区别于文学的独特性意义。1977年的电影《卡车》里,声画也有分离,但是杜拉斯和德帕迪约的“她说”将画面和声音变成了一个整体,她是女人也是杜拉斯,他是卡车司机也是德帕迪约,于是,在故事的讲述中,在讲述的连接中,两个画面潜在的叙事被并置在了一起。更重要的是,玛格丽特在其中阐述了一种“生成”的电影,热拉尔·德帕迪约问:“这原本是一部电影?”玛格丽特·杜拉斯回答:“这原本是一部电影。——这是一部电影。”问和答恰好了解构和建构的双重回路:德帕迪约的问题是对于这原本是一部电影的疑问,疑问指向的是有限的否定;杜拉斯的回答在前半句是对于这原本是一部电影的肯定,但是转折又变成了对原本是一部电影的否定,因为“这是一部电影”,因而成为了一部电影——从原本的电影变成了生成的电影,而且是正在生成的电影。
在1981年的电影《阿伽达与无限阅读》中,杜拉斯第一次以“阅读”命名这部电影,也将阅读放置在了无限的状态下:电影如何被阅读?阅读如何成为无限之可能?杜拉斯在电影中引入了纯粹的文字,在一定程度上让文字代替声音,是对于文字有限论的一次尝试,使得这部电影更像是可以被阅读的小说,在小说在电影中被阅读的同时,是不是意味着电影也可以通过文字得到阅读,“无限阅读”不是极端阅读,它在小说和电影双向道路上构建了阅读的可能。电影是通过小说生成的,电影和小说一样可以带来“无限月读”的可能,杜拉斯显然有限探寻着属于电影都有的叙事规则和意义。她的最后一部电影《孩子们》是更大的回归,一个永远7岁的孩子,一个看起来却是40多岁的孩子,在画面的传达中变成了一个寓言,电影的主体是对“孩子们”的自我保护,它在不被外界轻易改变中存在,他在思考,他在学习,他在成长,永远在自我世界里,这像是杜拉斯对文学叙事的偏执,但是“孩子们”得到了父母、老师的理解,得到了社会的肯定,“如果有人能理解,那就只有他自己,理解一定程度上就是说不出来。”
从执着于“她说”到意识到“说不出来”,玛格丽特·杜拉斯从自我构建的乌托邦和文字迷宫中有限地打开了一扇窗,文字是语言,文字是写作,电影也是语言,电影也是写作,不管是文字还是电影,都不是封闭的结构,也不是谁必须杀死谁的终极命题,它会自我生成,它具有无限可能,因为,“这是一部电影。”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7315]


